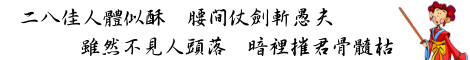第一 其心不殺
何謂殺?凡對人與物直接或間接戕其生命,傷其肢體,及絕其生機,均名為殺。若對人與物能不戕其生命,不傷其肢體,并不絕其生機,直接固不為,間接亦不為,如是始名為不殺。
然有時對人與物雖尚無殺之行為,而隱微之間,幽獨之內,須臾之頃,一念忽生,或欲有所中傷於人與物,或欲有所不利於人與物,或欲有所報復於人與物,雖是時殺業未成,然殺機即隱伏於是。他日對於人與物所以敢於發難,輕於動作,忍於戕殘者,其端實始於此時之一念。故當此一念發生時,雖非身殺,實已名為心殺。
身殺之罪惡在後,心殺之罪惡在先。身殺之罪惡甚著,心殺之罪惡至隱。身殺之罪惡易防,心殺之罪惡難制。身殺之罪惡有數,心殺之罪惡無窮。
心殺之罪惡,在孔孟之教說—為不仁,為無惻隱。在耶墨之教說—為不能忍,為非博愛。在釋氏之教說為不慈悲,為造惡因果。而其禍患之所至,能使人群之愛力稀微,社會之風俗澆薄,國家之團結力渙散,以至造成種種戰爭慘殺之劫運。故修心之道,不惟戒身殺,尤貴戒心殺。
戒心殺者之處心當如何?遇人與物之不如我意者,當諒而恕之。遇人與物之敢於忤我者,當犯而不校。當念人與物之行為,或因無知而誤陷於非,而我自身之意見,亦未必無所偏而悉合於理。苟能隨時隨事如是思維,則瞋念泯而殺機息矣。
戒心殺者,當念殺意之生,確有因果之應。蓋愛人者人愛,敬人者人敬。苟反乎是,則害人者人害之矣。害人為因,被人害為果。因果相乘,捷於影響,然此尤其顯著易見者耳。戒心殺者,當知殺業之成,非必盡由刀杖,往往一語言之末,一舉動之微,當時在我或只圖快心逞意,或不過附和隨聲,原未嘗料及戕害其生命,然因我一言一動之影響所及,竟致彼生計敗壞,生機斷絕,終遂及於危敗。故其造禍之主因,果報之追咎,當然不在他人而獨在我。
又戒心殺者,當念慘殺之苦,不因人物而殊。我愛生命,物類亦愛生命。我知痛苦,物類亦知痛苦。我貪安全,物類亦貪安全。奈何今縱我欲,任我之意,逞我之氣,貽彼以傷殘斷折之痛,撲滅離析之苦。須知彼物類所以愚弱,而易為人制伏戕賊者,實由其歷劫以來造作無量種種罪惡,於是智慧日消,福德日損,以致墮落沈淪於物類之畜生道中,受此無量苦惱。若我今者復造此罪惡——最大之殺業而尤傚之,則墮落沈淪之苦,行將及我矣。是故戒心殺者,對於人與物之生命,當隨時隨地存保護心,生惻隱心,起憐憫心,發慈悲心,盎然充滿,無乎不在。由是擴而充之,故能愛大群,利民生,惠庶物。凡愛人愛物之良法美舉,無不當以此實心行之,斯仁政遍及於宇宙萬物,有何殺運之不可挽回,人心之不良善也哉?
或曰:司法者在誅一儆百。勢不能以無殺。奈何,答曰:此有先決之問題二:一、民刑法之不良者,必求改良,以合於天理人情之至。二、執政者當力謀教養,使民不至罹陷於刑網。此二者實牧民之先務。若已能如是,而民仍犯法,則司法者固當執法以繩,但如得其情,必哀矜而勿喜,苟如是存心,斯已近於不殺矣。
或曰:將兵者貴鋤暴安良,勢更不能以無殺。奈何?答曰:矢人惟恐不傷人,最初固應慎於擇術,至業已廁身軍界,則凡一命令,一指揮,均在在與多數之民物生命有關,詎可不異常審慎。要以不妄傷一人一畜一草一木,為存心之標準。但使將兵者慎選軍徒,嚴明紀律,平日多所訓誡,臨時多所約束,無論戰事勝負,務禁騷擾凶殘,苟如是存心,雖躬行殺人之任務,然其勝殘去殺之心,亦可天人共鑒矣。昔鄧禹將兵百萬,自言時時注念,未敢妄殺一人,天道好還,吾後世必有興者。果也,禹之子孫,貴顯累世,封公侯者三十人,大將軍以下十六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郡牧守不可勝數,孫女、曾孫女均為帝后,亙十餘世不絕,積善降祥,寧或爽歟?
或曰:人類飲食,世俗宴會,久尚宰烹,勢又不能以無殺。奈何?答曰:不殺微命,不踐蟲蟻,假蔬食以衛生,近世善根深厚,智慧傑出之士,已優為之。固未嘗不可取以為法,其暫病未能者,所需肉食之類,應先戒於自宅內殺生,此外則因我一人特殺者不食,為我見殺者不食,為我聞殺者不食,此於飲食衛生,友朋酬酢,辦公營業,均可無所妨礙。倘能如是行持,亦庶幾暫可涵養不殺之心,而稍減少殺業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