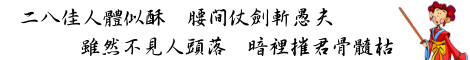難行之道
既然沒有人能救我們,也就是說沒有人能奇跡似的令我們開悟,我們現在所談之道乃名「難行之道」。此道不合乎我們的期望;我們所期望的是:涉入佛教是一段溫和、愉快、充滿慈悲的過程。其實,此道難行,是硬碰硬的心對心:你若敞開自心,願意相晤,則上師也會敞開其心。這裡面沒有奇跡可言,敞開是雙方共同創造的情況。
通常,一談解脫或悟道,我們就以為這些成就無需自己動手,會有別人幫忙。「你沒問題,不用愁,不要哭,你將安然無事,我會照顧你。」我們總以為自己所須做的,只是宣誓入會、繳入會費、簽名登記、遵命行事而已。「我深信你的組織是有效的,能解決我所有的問題。你怎麼給我安排都可以;如果你想要讓我吃苦受罪,請便。我什麼都聽你的。」這種除了遵命別無他事的心態,令人覺得安適。什麼都交給別人去辦,讓別人教導你和改正你的缺點。但我們卻大吃一驚的發現,實際情形並非如此,認為自己什麼都不用做的想法,完全是打如意算盤。
通過修道的種種困難,而正確的深入人生實況,需要極大的努力。因此,難行之道的重點似乎是修學者個人必須勉為其難,承認自己的真面目,摘下自己的假面具。你必須肯自立自強,難就難在這兒。
這並非說,難行之道是要我們非做英雄不可。英雄的氣概是建立在假定上;假定我們不好、不淨、沒有價值、沒有悟道的本錢,以致我們必須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例如,我們若是中等階級的美國人,那就必須放下工作、退學、搬出郊區的家、留長頭髮,或許還吸食毒品;我們若是嬉皮,那就必須放棄吸毒,剪短頭髮,丟掉破爛的牛仔褲。我們以為自己能不受誘惑就是與眾不同,就是英雄作風。我們成了素食者,成了這個那個。我們想成為的,太多了。我們以為自己是在修道,因為我們現在所做的與過去完全不同,但這全然是冒牌英雄的行徑,而此冒牌英雄,非「我」莫屬。
我們可以把這種虛妄的英雄行為發揮至極,而去修那極端的苦行。即使我們所信之教要我們每天倒立二十四小時,我們也會照辦。我們淨化自己、修行苦行,自覺已是毫無污點,改過自新,很有道德。或許當時看來這沒什麼不對。
我們可能試圖模仿某些修行之道,如美國印地安人的宗教之道、印度教之道或日本佛教的禪道。我們會從頭到腳換裝,學他們的打扮。或許我們的決定是去印度北部跟西藏人打成一片。我們可能穿上西藏的服飾,遵守西藏的習俗。這看來會像是「難行之道」,因為在此道上老是有障礙和誘惑來分我們的心,讓我們難以達到目的。
我們坐在印度教的靜修之所,有六、七個月沒吃巧克力了,所以我們心裡想著巧克力或其它我們愛吃的東西。我們也許懷念以前過耶誕節或新年時的情景,但是我們仍舊認為自己已找到修行之道。我們已奮力通過此一道上的種種困難,如今已能勝任愉快,成了某種修行的大師了。我們期望修行所產生的神奇力量和智慧能令我們進入正確的心境。有時我們認為自己已達成目標,我們也許一連六、七個月都是「飄飄欲仙」或如癡如呆;後來,我們這種心醉神迷的狀態又不見了。它就是這樣忽來忽去,時有時無。對這種情形,我們該怎麼辦?我們可能有很長一段時間都「飄飄欲仙」或充滿喜悅,但最後還是要降下來恢復常態。
我不是說外國傳統或持戒傳統不適用於修道,而是說我們誤信其中有能令我們獲得正確心態的妙方。這似乎是把問題本末倒置了;我們希望能從操縱物質或自然界當中獲得智慧和解悟,我們甚至期望科學大師們替我們做。他們可以把我們送進醫院,用適當的藥劑把我們的意識提升到崇高的境界。但我認為這是無法如願的事,我們無法擺脫自己的真面目,它永遠跟著我們走。
我們回過頭來要說的是,我們若想完全敞開自己,那就須有某種真正的佈施或奉獻。這種佈施不拘形式,但若要使我們的佈施真有意義,我們就必須不望回報。我們具有多少頭銜、穿破多少外國服裝、懂得多少哲理、發過多少誓願、參加過多少神聖儀式,這些都無關緊要;要緊的是我們必須佈施而不望回報。這是真正的難行之道。
我們也許暢遊日本。我們也許喜歡日本文化,喜歡日本的莊嚴禪寺和華麗藝術品。這些經驗不僅讓我們覺得美妙,同時也傳給我們一些訊息。日本的文化是出於日本的整個生活方式,而日本的生活方式又與西方的生活方式迥異,因此日本文化對我們有話可說。但文化的精緻和形象的優美究竟能對我們起多大的震撼,與我們有多大的關聯?我們不知道。我們只是想回味美麗的記憶。我們不想對自己的經驗過於深究。那是敏感地帶。
或許某位上師在一個非常動人、極有意味的儀式上為我們灌了頂。那項儀式真實、直接、莊嚴,但我們對此經驗肯提出多少疑問?那是私事,太敏感而不能問。我們寧願把那次美妙的經驗貯存起來,以便在日後境遇不順、心情沮喪時,拿來回憶一下,安慰自己,告訴自己我們真的作過有價值之事,真得入道了。這一點也不像是難行之道。
相反的,我們像是一直在收集,而不是在施捨。我們若仔細回想自己的求道過程,我們能記起自己曾經做過那些完全而又適當的佈施,曾經敞開過自己而施捨一切嗎?我們是否摘下過假面具,脫掉過甲冑,剝去過皮、肉、血管,直到內心?我們真的有過剝去、敞開、佈施的經驗嗎?這是根本問題。我們必須真正放下、有所施捨,即使非常痛苦,也要勉為其難。我們必須動手拆除我們一手造成之「我」的基本結構。拆除、脫掉、敞開、放下的過程,是真正的學習過程。這種指甲長入肉內的情況,我們已決定放棄多少?很可能我們根本沒想放棄任何東西。我們只是一直收集、建造,一層一層往上蓋。因此,展望難行之道,很能令人怕怕。
問題在於我們想找一個輕鬆無苦的答案。但這種解答不適用於修道,而修道一途是我們之中的很多人根本不該走上去的。一旦上去了,就會很痛苦,而且下不來。我們自願受暴露自己之苦,受脫掉衣服之苦,受剝去皮膚、神經、心、腦之苦,直到我們完全暴露在宇宙之前什麼都不剩。這會很可怕、很痛苦,但修道就是這樣。
不知怎麼回事,我們發現身旁有位陌生的醫師,他要給我們開刀,但不給我們麻醉,因為他真想跟我們的疾病溝通。他不准我們擺出修道的門面、玩弄心理的詭辯、偽裝心理上有病,或戴著其他假面具;我們但願從未遇到這位醫師,我們但願能自行麻醉。可是,我們已被套牢,跑不掉了。這不是因為他的力量大,我們本可跟他說聲再見就走;然而,我們已經向這位醫師暴露了那麼多,如果換個醫師從頭再來,那將非常痛苦,我們不願多受一次罪,所以只好硬撐到底。
跟這位醫師在一起,我們覺得很不舒服,因為我們老是想要騙他,儘管我們知道他能看穿我們的把戲。不施麻醉的手術是他跟我們溝通的唯一之道,所以我們非接受不可;我們必須對難行之道或這種手術敞開自己。我們越問「你要對我怎樣」這類的問題,我們就越侷促不安,因為我們曉得自己是怎麼回事而明知故問。難行之道是一條極其狹窄而又無法脫離的苦路,我們必須完全放下自己去與這位醫師溝通。此外,我們還須放下對上師的奢望,不再眼巴巴地盼望上師表現奇跡,以某種非凡無苦的方式給我們灌頂。我們必須不再尋求不痛的手術,不再希望他用麻醉劑或鎮定劑讓我們醒過來時只見一切完美。我們必須願意以完全敞開、直接、沒有任何死角的方式,與我們的道友及我們的生活溝通;難行之道就是這麼艱苦。
問:暴露自己是自然發生,還是有什麼方法使其發生或令自己敞開?
答:我想,你若已經投入暴露自己之道,那麼你越無為,敞開之道就越明顯。我認為敞開是自動的,並不要你非做什麼不可。在開始談放下時我說過,一旦你已向道友完全暴露自己,你就什麼都不用做了。這是只管如實接受現狀,而現狀則是我們反正都要接受的。我們常常發現自己處於赤身裸體而希望有衣遮醜的情況,這種窘境是我們在生活中總會有的遭遇。
問:我們是必須先有個道友,然後才能暴露自己,還是只對生活情況暴露自己就行?
答:我想,你需要一位看看你做的人,因為那樣你會覺得更為真實。在沒人的房間脫衣服容易,在人多的房間就難為情了。
問:這麼說來,我們其實是把自己暴露給自己?
答:對,但我們不這麼看。我們強烈地感覺到有觀眾在旁,因為我們的自我意識太重了。
問:我看不出苦行或持戒為何不是「真正的」難行之道。
答:你能欺騙自己,自以為是在修難行之道,其實不是。這就像是在一出英雄劇裡,英雄事跡含有很多「溫柔之道」,而難行之道則多屬於個人。做過英雄之後,你還有難行之道要走,這是很能令人震驚的發現。
問:是否必須先走英雄路,不屈不撓地走下去,然後才能走上真正的難行之道?
答:我不認為如此。這正是我要指出的。如果你走上英雄之路,你的個性便會加上層層的皮,因為你有成就感。後來你卻吃驚地發現,你所需要的是別的,於是你又得把加上的皮層層剝掉。
問:您說有受難忍之苦的必要。理解摘下假面具的過程就能無須受苦了嗎?
答:這是個微妙的問題。理解不是真做,只是懂了。你能理解受苦刑的人生理起何變化、心理感受如何,但實際的體驗完全是另一回事。光是理解痛苦不夠,你必須實際體驗。唯有親身體驗,才能接觸問題核心,但你不必製造苦境。有了手持利刃的醫師道友在旁協助,苦境自會出現。
問:如果你正在放下的過程當中,此時你的道友似乎要對你開刀而又解除你的麻醉,那可是極為恐怖的情景;你的道友好像很生氣、很厭煩,讓你想逃。您能否把這種情形說明一下?
答:重點就在這兒。難行之道是不施麻醉的手術,你必須願意接受才行。你要是跑了,那就像盲腸需要開刀而跑出手術室的病人;他的盲腸可能因此潰裂。
問:但我要說的是你跟道友初識的階段。相晤不過五分鐘,突然,屋頂塌了下來,而他卻一走了之,留下爛攤子讓你收拾。或許他還丟下幾句話:「你要走的路,我不陪你走。五分鐘已過,放棄這條路,完全放棄它,自己看著辦,等你完全擺脫了它的時候,我再跟你談。」我得到的感受就像這樣。
答:你要知道,這跟初學、宿學無關;問題全在你跟自己相處多久。你若曾跟自己相處,必然瞭解自己。這有如一種普通疾病;假定你到各國旅遊,途中病了,決定就醫。這位醫師只能勉強用你說的語言跟你交談,但是他能觸摸你的身體,看出你的病因,而決定把你送進醫院開刀。這全要視病情的輕重而定。手術的緩急要跟著病情惡化的程度走,遲了就完了。如果你患盲腸炎,而醫師遲遲不動刀,或許是為了要先跟你交個朋友,那麼你的盲腸就有可能潰裂。你不會說這是良好的行醫之道吧?
問:為何有人要邁出修道的第一步?是什麼引導他修道的?是意外、命運、業力,還是什麼?
答:你若完全暴露自己,你就已經是入道了。如果你只暴露一半,那麼你也只有部分入道——付出多少,收回多少。如果你對醫師該說的不說,你便會復元得很慢,因為你沒把自己的整個病歷告訴醫師。你告訴醫師的越多,醫師越能令你速愈。
問:如果真正的難行之道是暴露自己,那麼我該不該把自己暴露給我心目中的惡者,明知自己可能會受到傷害?
答:敞開不是一遇威脅就挺身而出,做個烈士。你不必面對疾馳而來的火車敞開自己。那是逞英雄,不是真正的難行之道。
每當我們面對心目中的「惡者」時,它就對「我」的自保構成威脅,在此威脅面前,我們忙於自保,根本無暇看清威脅我們的是什麼。要想敞開自己,我們必須突破自我保全之欲。這樣,我們才能看清實況,切實應付。
問:這不是一次完成的事吧?是嗎?我的意思是說,你在某種情況下敞開自己,但在另一種情況下,你卻又突然戴上了面具,雖然你的確不想這麼做。完完全全地敞開似乎是很難得的。
答:問題就在奮鬥與敞開毫不相干。你一走上了修道之路,不奮鬥就沒事,也就不再有想不想要涉人生活情況的問題。「我」那善於模仿的猴性也消失了,因為它是基於二手資料,而不是基於如實的直接體驗。奮鬥是「我」。一旦你不再奮鬥,就無征服奮鬥者,奮鬥自然消失。所以你看,這不是一件要把奮鬥打敗的事。
問:為了敞開自己,你該不該一怒就發脾氣?
答:我們講的敞開和放下,以忿怒時為例,並不是說你要真的跑出去見人就打。那似乎是在滿足「我」的需要,不是在適當地暴露你的忿怒,而適當地暴露忿怒就是如實看清忿怒的激烈本質。這一點通用於在各種情況下的暴露自己。問題是要如實看清情況的本質,而不是要有所作為。當然,你若毫無偏見的對情況完全敞開,便會知道怎麼做是對的,怎麼做是不智的。如果某種做法不智,你當然不會走那條路,而會選擇明智、富有創意之路走。你並非真地用心抉擇,但你必會走那有創意之路。
問:收集東西和為偽裝辯護是無可避免的階段嗎?
答:我們先是收集東西,後又跟這些東西變得難分難捨。這就像手術過後皮膚上留下了縫合傷口的線。我們害怕拆線,因為我們已對自身中的外來物感到習慣了。
問:您認為沒有上師也有可能開始看清實相,看清自己的真實面目嗎?
答:我認為根本不可能。你必須有個道友,才能放下和完全敞開自己。
問:這個道友一定要是活人嗎?
答:對。任何其他你自認為能與之溝通的「對像」,都是想像出來的。
問:基督教義本身可做道友嗎?
答:我不認為如此,那是想像的情況,任何教義都是這樣,並不限於基督教義。問題是我們可以自行解說,問題全在這兒:寫成文字的教義總免不了任由「我」講。
問:聽您講敞開自己和暴露自己,很能令我聯想到某些學派的心理療法。您看心理療法之所為有何作用?
答:大部分的心理療法都有這個問題:你雖說把心理治療的過程看作「治療」,其實你的真正意思是說它是一件有治療作用的事。換言之,這種治療對你是一種嗜好。而且,你把你的治療情形看作完全受制於你的血統和病歷等過去發生之事。由於過去你跟父母的關係不好,如今你才有了這種不良的性向。你一旦開始討論某人過去的一切,試圖把過去與現在連在一起,那人就會產生在劫難逃、無可救藥的感覺,因為他無法取消過去。他自覺為過去所困而無路可走。這種治療的方法極其不智,且很有害,因為它不讓你涉及此時此地正在發生之事所具有的創造性的一面。反之,如果心理療法強調生活在當下一刻、致力於眼前問題,不只是嘴巴說、腦子想,同時還切實體驗真正的感受,那麼我就認為它是很妥善的療法。不幸的是,有很多心理療法和心理治療醫師,都只顧證明自己和自己的理論是對的,而不管現實是怎麼樣。實際上,他們還覺得面對現實是恨可怕的事。
對任何理論方面的問題,我們都應予以簡化,而不要把它弄得很複雜。當下的一刻,即含過去的全部和未來的走向。因為一切全在這兒,所以我們不必到別處去找答案來證明我們過去是誰、現在是誰或未來可能是誰。我們一想要揭開過去,我們現在就捲入了雄心和奮鬥,而不能如實接受當下的一刻——這是非常懦弱的做法。此外,我們也不宜把我們的醫師或上師視為我們的救主,我們必須在自己身上下功夫。我們實無選擇的餘地。在某些情況下,道友也許會加重我們的痛苦,而那是醫師與病人關係中的一部分。我的意思是,不要把修道看作豪華舒適和輕鬆愉快,而應只視之為如實面對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