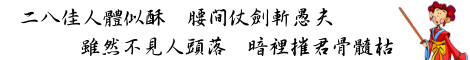灌頂
我的學生,大多是因為聽說我是禪師和西藏喇嘛才來跟我學的。但我們的初次邂逅如果是在路上或餐館,還會有多少人來呢?很少有人會因這種偶遇而起學佛修禪之心。引人學佛似乎是我的身份——從異國來的西藏禪師,第十一世創巴活佛。
人們就是這樣才來求我灌頂,以便加入佛教和修道的團體。但灌頂的意義究竟為何?佛法悠久偉大傳承的智慧是由禪師代代相傳的,且與灌頂有關,這又是怎麼回事?
在這方面憤世嫉俗一番,似乎值得。人們想要接受灌頂:他們想要加入這個俱樂部,得到頭銜,獲得智慧。我個人不想玩弄人們希求非凡之物的弱點。有些人買畢卡索的畫,只是因為畢卡索之名,他們願意付出高價,而對所買的藝術品是否值此價錢連想都不想;他們買的是畫作的證件或畫家的名氣,以名氣和傳聞作為藝術品質的保證。這種做法,可說是全無理性的思考。
有人可能因為覺得內心飢渴或自己無用,而參加俱樂部或有錢的組織,以便得吃得喝。他如願以償被養肥了,可是那又怎樣?誰在騙誰?是上師自欺、自大嗎? 「我有這麼受過灌頂的信徒。」還是上師欺騙弟子,誤導他們自信比以前更有智慧、更有道心,只因他們加入了他的組織,有了僧侶、瑜伽士或別的頭銜?這些名稱和證件真對我們有益嗎?當真有益嗎?我們要面對事實:半小時的儀式並不能提高我們的覺悟層次。我個人對佛教傳承和法教之力都極為信仰,但不是不加深思就照單全收的。
我們對修道一事必須慎思明辨。如果去聽上師說法,我們不該讓自己被他的名氣和神奇的能力迷住,而應善自體會他所說的每一句話和他所教的每一種修法。我們必須跟法教和法師明確而理智的打交道。這不是傻呵呵地接受堂皇的證書,也不是為了自利而參加俱樂部。
這不是找一位聰明的上師,以便買他的智慧或偷他的智慧。真正的灌頂,包涵率直的跟自己和道友相處。是故我們必須力求坦白,發露自欺,我們必須將自我的粗俗品性毫不保留的全交出來。
「灌頂」的梵語是abhisheka,意謂「灑」、「灌」、「塗油」。要灌,就要有可灌的容器。如果我們真心投入,對道友完全敞開自己,讓自己成為堪受告誡的容器,那麼道友也會敞開,灌頂於是發生。此即灌頂或師徒間「心心相印」的意義。
這種敞開,不含逢迎,沒有取悅或感動道友的企圖,就像醫生知你有病,必要時他會強行把你從家中移送醫院,未施麻醉就動手術。你可能覺得這種處治太野蠻、太痛苦,但也因而開始領悟到真正的溝通——如實與人生接觸——須付多大的代價。
依止某位上師,為宗教出錢出力,都未必是說我們已真的完全敞開自己了,此類行為更有可能只是變相的舉證,證明我們已加入「對」的一邊。上師似乎是有智慧的人,他曉得他在做什麼,我們想站在他那一邊——安全的一邊、善良的一邊——以便獲得福祉與成就。但是,我們一旦屬於他那一邊——清醒的一邊、穩定的一邊、智慧的一邊——我們便會發現,我們根本未能確保自身,因為我們所投入的只是我們的門面、我們的甲冑;我們並未全身投入。
接著,我們被迫從後面敞開自己。我們大吃一驚地發現,原來無處可逃。我們躲在門面背後的行為被逮個正著,以致全身暴露;我們身上的填料和甲冑被剝個精光,再也無處可躲。太可怕了!我們那點虛偽和自私,全被揭露無遺。到了這個地步,我們可能會領悟到自己笨手笨腳的裝模作樣,一直是枉費心機。
然而,我們並不死心,還想為此痛苦的處境找出藉口,還想找出自保的辦法,找出令「我」滿意的解釋來說明此一困境。我們左看這個問題,右看這個問題,心裡忙成一團。「我」很專業,「我」行「我」素,效率高得不得了。當我們自以為是朝著讓自己空空如也的方向努力前進時,卻發現自己在往後退,意圖確保自身和填滿自我。這種混亂的狀況繼續加強,直到我們終於發現自己完全迷失了方向,失去了立場,沒有起點、中途和終點,因為我們的心已完全被自衛的措施所盤據。因此,除投降、放下之外,似乎別無他途。我們機智的想法和做法,都對我們無益,因為我們的想法多得教我們吃不消;我們不知如何抉擇,不知哪種想法能提供我們最佳的自修之道。我們滿腦子都是非凡、聰明、合乎邏輯、合乎科學的妙計,但總是主意太多,反而無所適從。
如是一來,我們終於會真正放下一切煩瑣,騰出一點空間,就此歇手罷休。這是灌頂真正發生的時刻,因為我們已經敞開,真正放下了一切,不再想有所作為,不再跟繁忙雜亂打交道。最後我們不得不知止了,這對我們來說可是甚為希有。
我們從所知、所讀、所受、所夢,設計出多種不同的防禦措施。但到最後,我們對何為真正道心起了疑問。只是想要虔誠、善良嗎?還是想要比別人知道更多,想要更加瞭解人生意義?道心的真義是什麼?我們家人常去的教堂及其所宣揚的教義對此都有現成的理論,但這些理論都太薄弱、不實用,不足以作為我們所要尋求的答案。於是,我們便與生來就信的教義和教條疏離了。
我們或許認為道心應是非常令人興奮和多采多姿的,那是依外國奇異的宗教傳統去探究自己。我們採取另一種道心,遵循某種行為方式,企圖改變自己的聲調、飲食的習慣和一般的舉止。但過一陣子,這種不自在的修道企圖會讓你覺得太笨拙、太明顯、太平庸。我們想讓這些行為模式成為我們的習慣或第二本性,但它們總是無法完全成為我們的一部分。我們雖極想讓這些「覺悟的」行為模式與我們自然合一,可是我們心裡依舊忸怩不安。我們開始懷疑:「如果我已按照某一傳統的經典所說行事,怎會這樣?這一定是由於自己沒弄清楚。當然是如此。但我下一步該怎麼辦?」儘管我們信守經典之教,迷惑依然持續,不安與不滿還是存在。一切全都不靈,我們沒跟法教搭上線。
此時,我們實在需要「心心相印」。若無灌頂,我們求道的努力成果,將是收集了一大堆與修道有關的東西,而非真正放下。我們收集了不同的行為模式、不同的言談、衣著、思想方式,以及完全不同的做法;這一切都只不過是我們收集來企圖強行加在自己身上的東西罷了。
真正的灌頂,出自放下。我們如實對現狀敞開自己,然後與上師真正溝通。不管怎樣,上師都是跟我們坦誠相處;只要我們敞開自己,願意放下所收集的一切,灌頂就發生了。不必有「神聖的」儀式。其實,視灌頂為「神聖」很可能是佛教徒所謂「魔女」的誘惑。「魔」象徵不正常的意向、不平衡的生活,「魔」遣其女來誘惑我們。當諸魔女干預心心相印的灌頂時,她們會說:「你覺得內心平靜嗎?那是因為你在接受修道的法教;在你身上發生之事與修道有關,這可是神聖的。」她們聲音甜美、所言中聽,把我們誘惑的認為這種溝通、這種「心心相印」,是件「大事」。於是我們開始產生更符合輪迴的心態。這與基督教對亞當吃蘋果一事的看法類似,都是誘惑所造成的。我們一把灌頂視為神聖,我們便開始喪失原有的精確與敏銳,因為我們已經心生計較了。我們聽到魔女在向我們慶賀,說我們已經辦到了如此神聖之事。她們在我們四周跳舞、奏樂,假裝在這個儀式隆重的場合榮耀我們。
實際上,心心相印的發生十分自然。師徒在開放的情況下相會,雙方都明白開放是世間最微不足道的事。當我們能如是看自己和世間時,傳法就開始了。西藏傳統上稱這種對事物的看法為「平常心」。平常心最微不足道;它是完全開放,不作任何收集或評估。我們可以說這種微不足道意味深長,也可說這種平常實不平凡。但這種說法也只是魔女的另一種誘惑。歸根結柢,我們必須放棄想要非凡的企圖。
問:我似乎無法不想保全自己。我該怎麼辦?
答:你太想保全自己,以致那試圖不保全自己的想法成了一種遊戲、一大笑話、另一種保全自己的方式。你太用心監視自己和監視在監視的自己,以及監視在監視自己監視的自己;如是下去,沒完沒了。這是很普通的現象。
你真正需要的是完全不再關心,把你關心之事完全放下造了一具極好的測謊器,又造一具偵測測謊器的偵測器,這種疊床架屋的複雜結構,必須予以清除。你力求保全自己,而一旦獲得安全,你就又想確保那已經得到的安全。這種防禦工事,可以無限擴充。你也許只有一座城堡,但你的防禦工事可能遍及全球。如果你真想使自己絕對安全,你所能作的努力實在是沒有止境的。
因此,我們必須放棄保全自己的想法,看出力求自保的可笑,看出繁複的自保結構有多麼荒唐。你必須不再做監視監視者的監視者。要能做到這一點,你必須放棄第一個監視者,也就是放棄自保的企圖。
問:我不知道該提出何種國民性來討論,但是假如我們是印度人,您就不會這麼想了,會嗎?我的意思是說,由於我們是美國人,太愛做事,所以您才對我們這麼講。倘若我們不愛做事,整天游手好閒,您就不會對我們這麼講了。
答:這個問題很有趣。我想說法的方式要依聽眾在物質方面發展的快慢而定。美國現已達到極高的唯物層次。不過,具有這種發展物質文明的潛力的,不只是美國人,而是全世界的人。如果印度的經濟發展達到美國已達的階段,如果印度人也像美國人那樣嘗到唯物的滋味而感到幻滅,他們就會來聽這樣的演講了。但目前我不認為除了西方國家還有哪個地區會有人聽這種演講,因為其他地區的人對物質文明的發展還沒受夠;他們還在存錢買腳踏車,尚未到能買汽車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