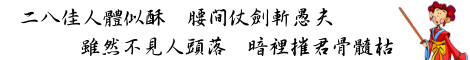上師
一學修道,我們便面臨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與我們認為能讓我們悟道的法師、喇嘛、上師或其他名稱的人之間的關係。這些名稱,特別是「上師」,在西方已產生了誤導的意義和聯想,常把「何謂跟上師學」這個問題弄得更加混淆不清。這並非說東方人知道如何與上師相處,而西方人不知;問題是普遍的。人們總是懷著成見來學修道,對於他們要學得什麼,以及如何與他們認為能傳授他們之人打交道,都已在心中有了固定的看法。相信自己從上師那裡能有所得,如:得樂、得心安、得智慧或得任何所欲得者,這種觀念即是最難克服的成見之一。因此,我認為仔細觀察某些著名弟子如何處理修道問題及如何與上師相處,對我們會有助益,或許這些實例會跟我們自己的探索有些關聯。
瑪爾巴是最有名的西藏大師之一,也是我隸屬的噶舉傳承在西藏的第一代祖師。他師事印度大師那諾巴,他最著名的弟子是密勒日巴。
瑪爾巴是一個完全靠自己努力而成功的典型代表。他生於農家,年輕時就心懷大志,選擇學術與僧職作為他成名之路。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一個農家之子,要能在當時當地的宗教傳統中,提升自己到僧侶的地位,必須付出多麼大的努力和有多麼大的決心。在第十世紀的西藏,像他那樣的人,要想得到一點名聲地位,只有幾條路可走,那就是經商、當土匪,或者是當喇嘛。在那個時代,要加入當地的僧團,大約就等於現今當上了醫生、律師和大學教授三者的總和。
瑪爾巴從學習語文入手,他學藏文、梵文、幾種其它語文和印度口語。這樣學了差不多三年,他就能以學者的身份開始賺錢了。他把賺來的錢都用在研究宗教上,終於成為一個普通的喇嘛。因為他所擔任的僧職使他在地方上小有名氣,但他並不以此為滿足,所以儘管他已結了婚,有了家眷,他還是繼續存錢,直到他積下了很多的黃金。
於是,瑪爾巴向親屬宣佈,要去印度搜集經教。當時的印度是世界佛學研究中心,也是那瀾陀大學的所在地,以及許多最偉大佛教聖哲的家鄉。瑪爾巴的目的是去研究、收集西藏沒有的經典,然後帶回來翻譯,使自己成為一位偉大的學者譯師。當時,甚至晚近,從藏赴印是一段漫長而危險的旅程。瑪爾巴的家人和長輩都極力勸阻他,但瑪爾巴已下定決心,結果就與一位也是學者的朋友一起動身了。
經過數月的艱苦旅程,他們越過喜馬拉雅山,進入印度,繼續向孟加拉前進。到了盂加拉,他們就各奔前程。由於在語言和宗教方面,兩個人的學識都很夠水準,因此他們決定各按自身所好,分別尋師。在分手前相約,來日再聚,以便結伴還鄉。
旅經尼泊爾的時候,瑪爾巴偶然聽人談到大名鼎鼎的那諾巴上師。那諾巴做過那瀾陀大學的校長。那瀾陀大學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佛學研究中心了。就在他事業達到巔峰時,那諾巴覺得自己所瞭解的只是教法的皮毛,而非真義。於是他放棄了校長的職位去尋找上師,他在帝洛巴上師那裡連受了十二年的苦,最後才得證悟。到了瑪爾巴聽說那諾巴名字的時候,那諾巴已被公認為是佛教中曾有過最偉大的聖人了。瑪爾巴當然要去找他。
瑪爾巴終於找到,那諾巴是住在孟加拉森林中一所簡陋的屋子,過著貧窮的生活。瑪爾巴原先以為,這樣一位大師的居所,一定是某種極其精緻和有宗教氣氛的建築,因而當時不免有些失望。不過他早已對印度的新奇事物感到不解,所以也就甘願不去計較了,心想:也許這就是印度上師們的生活方式吧!同時,那諾巴的聲望也壓倒了瑪爾巴的失望。瑪爾巴將帶來的金子,大部分都供養了那諾巴,並向他求教。瑪爾巴自我介紹,說他來自西藏,已婚,是喇嘛、學者和農夫,並說他不願放棄自己奮鬥得來的既有生活,而是進而想要收集法教,帶回西藏去翻譯,以便多賺點錢。那諾巴很輕易地就答應了,並給瑪爾巴說法開示。一切進行順利。
過了一些時候,瑪爾巴自己認為他所搜集的法教夠用了,於是準備返回西藏。他先到一個大城鎮的小旅館去,與原先同來印度的那位朋友會合,兩個人坐下來比較各自努力的成果。瑪爾巴的朋友一看瑪爾巴收集的法教,就哈哈大笑說:「這些法教一文不值!在西藏早就有了。你一定是找到了更令人興奮和稀罕的東西而沒拿出來吧!我就找到了奇妙的法教,都是從極偉大的上師那裡得來的。」
瑪爾巴感到非常沮喪、懊惱。千里跋涉來到印度,經歷了那麼多的艱辛,花了那麼多的錢,而所得竟是如此!他決心回到那諾巴那兒再試一次。回到了那諾巴住的小屋,他請求那諾巴,再教他更稀有、更有印度風味、更高級的東西。出乎意外地,那諾巴對他說:「抱歉之至!我無法教你這些東西,你得另請高明;此人名叫庫庫瑞巴(Kukuripa)。去找他可不容易,特別是因為他住在湖中的小島上,湖水全是毒水,如果你要想得到這些法教,你就非去見他不可。」
到了這個時候,瑪爾巴什麼都顧不得了,他決心前往。再說,庫庫瑞巴的法教,竟連那諾巴都傳授不了,可見他有多麼高明了,而且,既能住在毒湖之中,他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上師,一位偉大的神秘家。
就這樣,瑪爾巴動身了。他千方百計總算渡過毒水,上了小島,開始尋找庫庫瑞巴。結果他發現庫庫瑞巴是一位印度老人,與數百條母狗為伍,生活環境骯髒不堪,這種情形,要說它「怪異」是算最客氣的了。儘管如此,瑪爾巴還是趨前搭話,所得的回應卻是胡言亂語,不知所云。庫庫瑞巴所講的話似乎毫無意義。
當時的情況使瑪爾巴幾乎無法忍受。他不僅完全聽不懂庫庫瑞巴所講的是什麼,而且還要隨時提防那數百條母狗。每當他跟一條母狗混熟了,另一條又對他狂吠,作欲咬勢,最後弄得瑪爾巴簡直要發瘋。他放棄了一切,放棄了記筆記,放棄了求取任何密教的企圖。就在此刻,庫庫瑞巴又開口對他講話了。這一回說得清清楚楚,有條有理,狗也不再找他的麻煩了。瑪爾巴乃得以受教。
瑪爾巴在庫庫瑞巴處學完之後,又回到他原來的上師那諾巴那兒。那諾巴對他說:「現在你必須返回西藏,弘揚法教。只在理論上得到法教是不夠的,你還必須要在實際的生活情況中切身體驗,然後你可以再回來進修。」
瑪爾巴與他的朋友再度會合,一起動身開始了返藏的漫長旅程。他的旅伴也學得了不少,兩個人都有成堆的筆記。他們一邊走一邊討論彼此所學。不久,瑪爾巴就開始對他的旅伴感到不安。他的旅伴似乎對他所收集的法教問得越來越多,他們的談話似乎老是轉向這一方面。最後他的旅伴確認瑪爾巴所得到的法教比自己得到的更為寶貴,不免大為嫉妒。在渡船上,瑪爾巴的旅伴開始抱怨行李太多,坐不舒服,他假裝為要舒服一點而扭動身體,實際上則藉著扭動身體之便,把瑪爾巴的筆記全丟到水裡去了。瑪爾巴雖拚命設法挽救,可是已經太遲了。他花費那麼多的心血所收集的法本和經典,一瞬之間完全付諸東流。
瑪爾巴垂頭喪氣地回到了西藏。關於他的旅途見聞和學法情形,他有說不完的故事可講,而能證實他的學識與經驗的東西,卻一點也沒有。不過,他還是工作,又教學了好幾年。直到有一天,他驚奇的領悟到,他在印度所作的筆記,即使沒有丟,也沒有用。在印度時,他只把那些他不瞭解的法教記下來,而沒有記下那些已與他自身經驗融合一處的法教。過了這麼多年,他才發現那些法教確實已經成為他自己的一部分了。
有了這項發現,瑪爾巴原先靠教學賺錢的慾望完全消失。他不再關心自己的名利,而只是一心想要覺證。為了供養那諾巴,他又積聚砂金,再度赴印。這一次,他心中只是渴望見到他的上師和求得法教。
然而,瑪爾巴與那諾巴這一次的會面與前一次完全不同。那諾巴的態度似乎非常冷漠,幾乎含有敵意。那諾巴一開口就說:「能再度見到你,很好。你有多少金子可以來買法教?」瑪爾巴帶了很多金子,不過他想留下一些自用,並作為他返藏的旅費。所以,他打開口袋,只拿出一部分金子給那諾巴。那諾巴看了看他的供養,說:「不行,這不夠。要我教你佛法,還得多來點兒金子才成。把你的金子全都給我。」瑪爾巴又給了他一些;那諾巴要求更多。就這樣一來一往,討價還價直到最後,那諾巴大笑起來,說:「你以為能用你的欺騙來買我的佛法嗎?」聽了這話,瑪爾巴讓步了。他把所有的金子全給了那諾巴。瑪爾巴萬萬沒想到,那諾巴拿起裝金子的口袋,就把袋中的砂金全扔到空中去了。
突然之間,瑪爾巴感到極端的困惑和懷疑,因為他弄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曾為了買他想要的法教,努力積聚金子,而那諾巴似乎也曾表示需要金子,作為教導瑪爾巴的代價。可是現在那諾巴卻把金子全扔了!這時,那諾巴對他說:「我要金子幹什麼?整個世界都是我的金子!」
對瑪爾巴來說,這才是敞開求法的偉大時刻。他敞開了,他可以接受法教了。此後,他與那諾巴相處很久,接受嚴格的訓練。他不再像先前那樣,只用耳朵去聽法教,而是身體力行。他不得不放棄他所有的一切,不僅是物質方面的,還有他內心深處所隱藏的。這可說是一個繼續不斷地敞開與真正放下的過程。
密勒日巴在修道上的發展,情況與瑪爾巴頗不相同。密勒日巴是小農,學問與修養比瑪爾巴在見那諾巴時差得多,而且他還犯過多種罪,包括謀殺。他很苦悶,極想成覺,無論瑪爾巴向他要多少報酬,他都願意付。於是,瑪爾巴要他付出真得勞其筋骨的勞力。瑪爾巴叫密勒日巴為他一連建造多所房屋,每建好一所,瑪爾巴就又叫他拆掉,而且叫他把所有建屋用的石材全都搬回當初找到它們的地方,以免破壞風景。每次瑪爾巴命令密勒日巴拆房子的時候,都會提出荒謬的藉口,如當初叫他蓋房子時說的是醉話,或說從未叫他蓋這種房子。每次密勒日巴都因一心求法而遵命行事,拆了再蓋。
最後瑪爾巴設計了一座九層高摟。密勒日巴搬石建樓,身體遭受極大的痛苦。建好之後,他去見瑪爾巴,再度乞授法教。瑪爾巴卻對他說:「只因給我建了這座高樓,你就想從我這裡獲得法教,有那麼簡單嗎?恐怕你還得給我一分禮物作為拜師費才行。」
密勒日巴的時間和勞力全都用在蓋房子上了,以致此刻他已一無所有。幸虧瑪爾巴的妻子達媚瑪(Damema)同情他,對他說:「你蓋的那些房子,充分表現出你的虔誠和信心。如果我給你幾袋大麥和一匹布作為拜師禮,我的先生一定不會介意。」於是密勒日巴帶著大麥和布到拜師的圓壇去。瑪爾巴正在那裡說法,密勒日巴把自己的禮物跟其他弟子的禮物放在一起,作為拜師費。但當瑪爾巴認出密勒日巴所獻的禮物時,勃然大怒,對密勒日巴吼叫著說:「這些東西是我的,你這個假冒偽善的人!你想騙我!」然後他一腳把密勒日巴踢出圓壇。
到了這個地步,密勒日巴完全放棄了獲得瑪爾巴傳法的希望。於絕望中,他決心自殺,就在他正要動手的時候,瑪爾巴來了,說他隨時可以接受法教。
接受法教的過程,全看弟子如何回報;某種心理上的放下是必要的,這也可算是禮物。此即為何我們在談師徒間的關係之前,先要討論放下、敞開和放棄希望。放下自己、敞開自己,把你的真實面目呈現在上師面前,而不是要擺出一副堪受法教的弟子模樣。至於你願意付出多少,你的行為是如何中規中矩,以及你是多麼善於對上師說恰當的話,都無關緊要。這跟求職的面談或購買新車不同。你能否獲得那分工作,要看你的證件是否合格、你的衣著是否合宜、你的皮鞋是否擦亮、你的談吐是否文雅、你的禮貌是否周到。若是買車,那就要看你有多少錢,以及你的信用如何了。
但一談修道,那就需要有點別的。它不是要求職,不是要整肅儀容以便給未來的僱主一個好印象;這種虛詐,在跟上師面談時用不上,因為他能把你看穿。我們若為了跟他面談而特別打扮自己,他會覺得好笑。奉承在此不能適用,因為實在是枉費心機。我們必須認真坦對上師,我們必須甘願放棄所有成見。密勒日巴預期瑪爾巴是位大學者和聖人,身著瑜伽士服、項掛念珠、口誦真言、閉目打坐。實際上,他卻發現瑪爾巴在田間工作,指揮工人,耕耘土地。
「上師」這個名詞,在西方恐怕是被濫用了,不如以「道友」相稱為妙。因為法教強調心心相印,那是彼此溝通,不是崇高的開悟者與不幸的糊塗人之間的主僕關係。在主僕的關係下,崇高的開悟者甚至可能看來不是坐於其位,而是浮身於空,居高臨下,向我們垂視。他的聲音遍滿虛空,他的一言、一咳、一動,也都成了智慧的表現。但這是夢想,不是事實。上師應是道友,他把他的品性傳給我們、獻給我們,一如瑪爾巴之於密勒日巴,或那諾巴之於瑪爾巴。瑪爾巴呈現出他為農夫瑜伽士的品性,他有七個子女和一個妻子,他照顧他的農地,以種田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他愛護弟子,一如愛護莊稼和家人。他做事徹底,注意生活細節,以致不僅成為勝任的父親和農人,而且成為勝任的上師。瑪爾巴的生活方式裡,根本沒有肉體上或心靈上的唯物。他並不因強調道心而忽視他的家庭或他在肉體上與大地的關係。你若在心靈上和肉體上皆不唯物,那就不會偏重任何一端。
你若僅因某人赫赫有名、著作等身、信徒成千上萬,就選擇他做你的上師,那對你也是沒有助益的。你所應依據的準則該是看你能否與他直接、完全地溝通。你自欺的程度如何?如果你真的對道友敞開自己,那麼你就一定會跟他合作。你能適當的向他傾吐肺腑之言嗎?他對你有什麼瞭解?他對自己又知道什麼?這位上師真能看穿你的面具,而恰如其分的與你直接溝通嗎?尋求上師一事,似乎應以此為準,而不是根據他的名聲或智慧。
有一個有趣的故事,講到一群人決心去跟一位西藏上師修學。他們已經跟別的上師學過了,但又一心想要跟這位上師學。他們都急於要做他的弟子,因此都想參謁他,但這位大師全不接受。他說:「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我才肯收你們為弟子,那就是你們願意拋棄你們以前的上師。」他們都向他懇求,說他們對他是如何虔誠,說他的名聲是多麼偉大,以及他們是多麼想要跟他修學。但他還是不肯,除非他們能滿足他所提出的條件。最後,除一人外,其餘都決定拋棄過去曾對他們教誨甚多的那些上師。看到這種情形,上師似乎頗為高興,叫他們次日再來。但當他們再去時,上師對他們說:「我知道你們的偽善。下一回你們去找另一位上師的時候,就會拋棄我了。滾出去!」說完,他便把他們全都趕走,只留下珍視其過去所學的那位,因他不肯玩騙人的把戲,不肯為了取悅上師而掩飾自己的真面目。你若想跟上師交友,就必須單純、坦白地去交,這樣才能有對等的溝通,切莫企圖贏得上師的青睞。
若要讓上師肯以你為友,你必須完全敞開自己。若想敞開自己,你可能要接受道友和日常生活狀況的考驗,所有這些考驗都是以令你失望的姿態出現。在某一階段,你會懷疑道友對你完全無情,這其實是在對付你的偽善。偽善或「我」的假面具和根本癖極其頑固——它的皮很厚。我們易於穿上層層甲胃。這種偽善十分濃密,具有多層,以致脫去一層又出現一層。我們希望不必全脫,我們希望只脫少數幾層就能見人了。我們穿著剛露出來的甲胃,面帶逢迎之色去見道友,但我們的道友卻全無甲胃,而是赤裸裸的人。跟他的裸體相比,我們簡直是水泥加身。我們的甲胃厚得讓道友摸不出我們的皮膚,摸不出我們的身體,甚至連我們的面目都看不清。
有許多故事講過去師徒的關係,說那時弟子必須長途跋涉,受盡千辛萬苦,直到他的迷惑和衝動開始衰退。重點似乎就在此。有所追求,本是一種煩惱;當此衝動開始衰退時,我們的本來面目即開始出現,同時也開始有了心與心的溝通。
曾有人說,與道友會晤的第一階段,猶如去超級市場;你很興奮,夢想著你要買的各種東西,也就是夢想著道友的富足及其個性的多采多姿。第二階段的彼此關係,猶如上法庭,你像是犯了罪似的;你無法滿足道友的要求,而開始覺得不自在,因為你曉得他對你的瞭解跟你對自己的瞭解一樣多,這是很令人不安之事。在第三階段,去見道友猶如去看草地上欣然吃草的牛;你只是讚歎牛的安詳和該處的風景,隨即繼續前行。最後,與道友交往的第四階段,猶如途徑一塊岩石;你看都不看它一眼,只是從旁走過而已。
起初,你有取悅上師的表現,猶如求愛,你關心的是能贏得上師多少青睞;你想要親近道友,因為你真想修學。你對他極感欽佩,但他又非常可怕;他老是把你推開。因此,不是情況不如你所期,就是你有一種不自在的感覺:「我可能無法完全徹底敞開自己。」於是,一種愛恨交織的關係,一種放下、逃走的過程,逐漸產生。換言之,我們開始玩遊戲,玩一種想要開放、想要與上師戀愛,結果又想離開上師而逃的遊戲。我們若與道友過分親近,便會生起受制於他的感覺。誠如西藏的古老格言:「上師如火,近之則被燒傷,遠之則不夠熱。」這種求愛的情形會發生在弟子身上——你易於過分親近上師,但一如此就被燒傷。於是你便想一走了之。
你與上師的關係,終於落實而靠得住了。你開始明白,想要親近上師或想要疏遠上師,全是你自己玩的把戲。它與實際情況無關,只是你自己的幻想而已。上師或道友始終在那兒燃燒,始終是生命之火,跟不跟他玩遊戲,任由你選。
接著,你與道友的關係變得極具創造性——你接受被他壓制和被他疏遠的情況。他要冷若冰霜,你接受;他要熱情如火,你也接受。什麼都不能動搖你,你跟他和解了。
下一階段是,在接受道友所做的一切之後,你開始失去自己的靈感,因為你已完全放下、完全放棄,你覺得自己縮成一粒微塵,微不足道。你開始覺得,唯一存在的世界就是這位道友或上師的世界。你好像是在看一場迷人的電影,情節是那麼扣人心弦,以致你成為其中的一部分。這時你沒了,電影院、椅子、觀眾,以及坐在你身旁的朋友,也沒了;唯一存在的就是電影。這叫「蜜月期」,於此期間一切都被視為上師這位中心人物的一部分,你只是一個毫無用處、微不足道的人,在不斷接受這位偉大、迷人的中心人物的餵養。你一覺得虛弱、疲倦或厭煩,就去電影院;只要往那兒一坐,便能得到娛樂、振奮而返老還童。此刻對個人的崇拜是最突出的現象——上師是世上唯一活生生存在的人,你的人生意義全繫於上師;你死是為他而死,你活是為他而活,你自己無足輕重。
不過,這種跟道友的戀愛無法永久持續;熱情早晚會消退,而你也必須面對自己的生活處境和自己的心理狀態。這就像結過了婚,度過了蜜月,你不再僅是感到你所愛之人是你注意的焦點,同時也開始注意他或她的生活方式。你開始注意,在上師的個性和人格之外,還有什麼使他成為上師。這樣一來,「上師無所不在」之理,也成了你的發現之一。你在生活中面對的每一問題,都是婚姻的一部分。一遇到困難,你就聽到上師所說的話。這是開始獨立,不再以上師為情人而分手的時刻,因為每一狀況皆表達法教。你先是對道友放下一切,然後是與他溝通、跟他遊戲。如今你已到了完全開放的境界。因開放故,你開始於每一個人生處境皆見上師品性,所有人生處境都讓你有機會像跟上師在一起時那樣開放,以致一切事物皆可成為上師。
密勒日巴在「紅寶石谷」這個嚴格的閉關之所修觀時,曾於幻象中清楚地看到他的上師瑪爾巴。由於餓得身體虛弱,再加上風吹雨打,密勒日巴在洞外撿柴時昏過去了。甦醒過來,他向東方望去,只見瑪爾巴住處那邊有白雲朵朵;他心懷熱望,唱歌祈求,傾訴他是多麼想跟瑪爾巴在一起,於是瑪爾巴在幻象中向他顯現。瑪爾巴騎著雪白的獅子,對他講話,內容大致是:「你怎麼啦?是不是在發瘋啊?你懂佛法,繼續修吧!」密勒日巴以此為慰,又回洞去修了。他對瑪爾巴的依戀,顯示出他當時尚未擺脫以上師為個人之友的觀念。
然而,當密勒日巴回到洞中時,他發現裡面全是魔鬼,眼大如湯鍋,身小如拇指。他想盡辦法,試圖阻止他們的嘲弄,但他們就是不肯離去,直到密勒日巴終於不再跟他們玩遊戲,而承認自己的偽善,並向開放讓步為止。從此時起,你可看出密勒日巴的歌風有了重大的轉變,因為他已學到了認同上師的普遍性,而不再僅以瑪爾巴為單獨的個人來跟他交往。
道友不僅是個人或外人,同時也成了你的一部分。如是一來,上師於內於外,都在透視和暴露我們之偽善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上師可做明鏡,能反映你,或者你自己的根本智顯現成為道友。當內在的上師開始發揮作用時,開放的要求就會咬住你不放。根本智如影隨形,老是跟著你;你躲不開自己的影子,總覺得:「老大哥在監視你。」事實上,監視我們和糾纏我們的不在於外;我們是自己糾纏自己,是我們自己的影子在監視我。
我們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我們可以把上師看作糾纏我們和嘲笑我們偽善之鬼。在瞭解自己的真相一事上,可能含有一種窮凶極惡的性質,但同時也總是有道友的創造性成為我們的一部分。根本智是不斷出現於各種生活狀況中的,此智銳利,無堅不摧,以致到了其一階段,即使你想擺脫它,也擺脫不掉。有時,它表情嚴肅;有時,它笑容可掬。密教有一傳統說法,那就是你看不見上師的臉,但隨時都看到他面部的表情。不管是微笑、咧著嘴笑或滿面怒容、皺著眉頭,全是每一生活情況的一部分。根本智、如來藏或佛性,永遠是每一人生經驗裡都有的,無法逃避。法教中還說:「最好不開始;一旦開始,最好完成。」所以除非必要,你最好不入修行之道;一旦踏上去,你就是已經真得做了,不能再退出,已是無路可逃了。
問:在多種修道中心偶然待過之後,我覺得像瑪爾巴那樣的人物,對大部分愛好此道者來說,是一種非常不易處理的現象,因為他的所為似乎完全不是一般所說的那種成就之道。他不修苦行,也不禁慾,他照顧日常的俗事。他是很平常的人,但他顯然又是具大能力的上師。瑪爾巴是唯一曾充分利用平常人的潛能,而無須修苦行、無須持淨戒的人嗎?
答:當然,瑪爾巴是發揮出潛能的實例,這些潛能是我們都有的。不過,他在印度時,確曾接受極其嚴格的訓練。他在印度大師的指導下,精進研學,為修道做好了準備工作。但我認為,我們必須瞭解「持戒」與「苦行」的真義。苦行或如法生活的觀念,基本上是要明智。因此,如果你覺得過普通生活是明智之舉,則普通生活即是如法生活;同時,你也可能覺得過經典中所描述的苦行瑜伽士的生活,會成為神智不健全的表現。這全視個人而定。問題是在你看來何為明智?何為真正踏實、穩當的人生觀?例如,佛陀不是企圖依某種崇高理念而行的宗教狂,他只是單純、坦白和非常明智地與人交往。他的智慧來自卓越的常識,他的法教健全、開放。
問題似乎是人們為宗教與褻瀆之間的衝突而擔憂。他們覺得很難將所謂「高等意識」與實際事務融合在一起。但是高低之分、宗教與褻瀆之分,似乎跟基本上明智的人生觀並非真有關係。
瑪爾巴只是個平常人,做著生活中的瑣事,他從來沒有想要做不尋常的人。動怒時,他就動怒打人;他直來直往,說做就做,從不拐彎抹角,虛偽矯飾。宗教狂就不同了;他們老是想要合乎某一理想的典範,他們企圖贏得人心,而所採取的方法是表現得非常熱烈和激昂,好像他們是純淨、純善。但我認為,企圖證明自己善良,就表示內心有所恐懼。瑪爾巴則無須證明什麼;他只是一個十分明智、實在的老百姓,同時也是一位大覺者。事實上,他是整個噶舉傳承之父,我們目前所學、所修的法教,無不出自於他。
問:禪宗有句話說:「先是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接著是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但最後卻是見山又是山,見水又是水。」我們現在是否都處於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的階段?但您一直在強調平凡。我們不是先要經過「非凡」期才能真的平凡嗎?
答:瑪爾巴有喪子之痛,當時他心中非常苦惱,有個弟子問他:「您常告訴我們一切是幻,那麼您的喪子一事又如何呢?難道不是幻嗎?」瑪爾巴答道:「是幻,但我的兒子之死是超級之幻。」
我們在初次嘗到真正平凡的滋味時,會覺得那是極不尋常的平凡,以致會說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因為我們之所見太平凡、太明確、太「如實」了。這種不尋常感,是有了新發現時的感受。但這種超級平凡,這種明確如實,終於變成司空見慣、無時無之、真正平凡,而我們也回到起點: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於是我們可以安心了。
問:你怎樣脫掉甲冑?你怎樣敞開自己?
答:那是你怎樣做的問題。敞開自己,並無儀式或公式。第一個障礙就在你所提出的問題本身:「怎樣?」你若不問自己,不監視自己,你就逕行去做了。我們不考慮怎樣嘔吐,我們逕行嘔吐,我們沒有時間去想要如何嘔吐,嘔吐便逕自發生。我們若是非常緊張,便會遭受極大痛苦,反而吐不好了;我們會力圖把要吐出的嚥回去,力圖跟病拚鬥。我們必須學習在有病時放鬆身心。
問:當生活情況開始成為你的上師時,情況為何,有關係嗎?你的處境怎樣,有關係嗎?
答:你沒有選擇的餘地。不管發生什麼事,都是上師的示現。情況可能是痛苦的或令人鼓舞的,但在這種視情況為上師的開放境界裡,苦樂如一,全無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