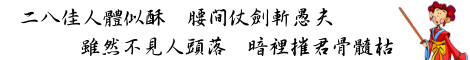六道
我們上次講完離開猴子的時候,它正在地獄道張牙舞爪、拳打腳踢,企圖衝破牢房之牆。猴子在地獄道的經驗恐怖極了。它發現自己走過大片熾熱的鐵地,或被鎖鏈繫住、畫上黑線、依線切割,或在熱鐵屋中烘烤,或在大鍋中燉煮。此類有關地獄的幻想,都是出自懼閉和瞋恚的背景,其中有一種陷在狹小空間,無法呼吸、無法走動的感覺。被囚的猴子,不僅想要摧毀禁閉它的牢獄之牆,甚至還想自殺,以擺脫那不斷折磨它的大苦。但它並不能真把自己殺了,它的自殺企圖只能加重它所受的折磨。猴子越力圖摧毀或控制牆壁,牆壁就變得越發堅固和沉悶;直到某一點,猴子強烈的瞋恚開始露出疲態:它不再跟牆壁作戰,不再跟牆壁來往,它變得麻木、冷酷,雖仍身在苦中,但不想逃了。此時,它受到各種各樣的折磨,包括挨凍和住在荒涼的地方。
不過,猴子終於奮鬥累了。地獄道的酷烈開始減弱,猴子也開始鬆弛;它突然發現自己的生活可以過得更敞開、更開闊。它渴望這種新境界,而這種新境界即是餓鬼道:貧窮和渴望救濟之感。在地獄道時,它太忙於奮鬥,以致沒有時間去想那得救的可能;如今在餓鬼道,它如饑似渴地希望過較為愉快和開闊的生活,而幻想出多種滿足其飢渴的方式。它在想像中也許看到遠處有敞開的空間,但走近時卻發現那是一大片可怕的沙漠;或許它看到遠處有一棵巨大的果樹,但走近時,卻發現樹上沒有果實,或有人在看守;或許它飛到一個看來蒼翠肥沃的山谷,但卻發現谷裡全是毒蟲,充滿腐爛的植物發出的惡臭。在每個幻想裡,它都瞥見滿足其欲的可能,而去追求時,卻很快就大失所望了。每當快樂似乎就要到手時,它卻冷不防地被從美夢中喚醒,但它的飢渴迫使它不屈不撓、繼續不斷地幻想未來的滿足。失望的痛苦,讓猴子對自己所做的美夢又愛又恨,它被美夢迷住了,但美夢的不能成真又教它對美夢感到厭惡。
餓鬼道之苦,主要不是苦在所求不得,而是苦在貪得無厭。如果猴子找到了大量食物的話,它很可能碰都不碰;不然就是通通吃光,還要更多。這是因為基本上猴子所迷戀的是飢渴的狀態,不是飢渴的滿足。它所有滿足飢渴的企圖都迅速遭到挫敗,以致它能一再回到飢渴狀態。如是,餓鬼道的痛苦與飢渴,就像地獄道的瞋恚和其餘各道的偏見一樣,提供猴子可寄托精神的有趣之事,可打交道的具體東西,或令它自覺實存的東西。它怕放棄這安全和娛樂,不敢踏入敞開空間的未知世界。它寧願待在它所熟悉的牢獄,不管它是多麼令它痛苦和鬱悶。
然而,就在猴子企圖實現其美夢而屢遭挫敗當中,它開始只得有些怨恨,同時也有些聽天由命了。它開始放棄強烈的渴望,而進一步放鬆自己,對外界只作習慣性的反應。它只依賴這一套反應,不理會其它應付人生際遇的方法,以致限定了它的世界。狗總是碰到什麼就嗅什麼,貓總是對電視不感興趣——此即愚癡的畜生道。猴子無視週遭的環境,不肯探勘新的領域,只是執著熟悉的目標和熟悉的煩惱。它陶醉於它的安全、自足、熟悉的世界,故將注意力集中在熟悉的目標上,並以堅定不移的決心去追求這些目標。因此,畜生道的象徵是豬,豬是鼻下有什麼就吃什麼;豬不左顧右盼,它直來直往,說做就做。是否必須游過泥沼或面對其他障礙,對豬來說,全無所謂;它只是勇往直前,面前有什麼就吃什麼。
但是猴子終於明白,它能於苦於樂有所選擇。它開始變得聰明一些,能夠分別苦樂的感受,而力求增樂減苦——此即分別心強的人道。至此,猴子不再盲目追求,而是對它所求的是什麼先加以考慮。它變得更有識別力,能考慮各種可能,想的更多,從而希望和恐懼相對增加——此即有熱情、有理智的人道。猴子變得更聰明了,它不再只是攫取,它還先行探勘、摸摸質地、比比貨色;一旦決定要什麼,它就盡力把它抓過來,據為己有。例如,如果猴子想要的是一塊漂亮的絲料,它會到不同的商店去摸摸各種絲料的質地,看看哪一種正是它想要的。找到完全合意或近乎滿意的絲料時,它會邊摸邊說:「啊,這就對了。不是很漂亮嗎?我看可以買。」它於是付款,把它買回家去,向朋友炫耀,請朋友摸摸看,讓他們鑒賞那塊漂亮絲料的質地。在人道,猴子總是想著如何擁有令它愉快的事物:「也許我該買個玩具熊陪我睡覺,買個可愛、讓人想抱、柔軟、溫暖、毛茸茸的東西。」
可是猴子又發現,它雖有智,能操縱它的世界,給自己帶來一些快樂,但它無法保持快樂,同時也不能總是要什麼就有什麼。它有老、病、死苦,遭受各種各樣的挫折與困難。它的快樂總是有痛苦為伴。
於是,它開始十分合乎邏輯地推斷出天道的可能——完全無苦、只有快樂的可能。它心目中的天道,也許是極端富有、極具權勢或極享盛名;不管它想要它的世界怎樣,它都一心求取,全力競爭——此即嫉妒的阿修羅道。猴子夢想著優於人道之苦樂的理想境界,老是想要達到那境界,老是想要出類拔萃。在不斷力求某種完美的奮鬥當中,猴子變得把心完全放在衡量自己的進展和跟他人的比較上。由於更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和情緒,猴子更能專一心志,故能比在人道時更有效地操縱它的世界,但它老是一心想要成為最好,一心想要主宰情況,以致有了不安全感和焦慮感。它必須不斷奮鬥以控制它的領域,克服一切對它所獲成就的威脅——它一直是在為擁有其世界的主權而作戰。
求勝的野心和戰敗的恐懼,不僅令它煩惱,同時也使它感到自己還活著。猴子經常忘了它的最終目標,但仍為它那期求更好之心所驅策。它被競爭與成就迷住了。它找出那些似乎非其能力所及的、快樂動人的境界,想要把它們拉入它的領域。當目標難以達成時,它會畏縮不前,退出戰鬥,而怪自己沒有嚴格鍛煉,沒有更加努力。猴子就這樣陷入一個理想落空、責備自己、害怕失敗的世界。
最後,猴子也許達成了它的目標,成了百萬富翁、國家元首或名藝術家。達成目標之初,它還會有不安全感;但它早晚會覺察自己已經成功、已達目的、已是身在天道了。於是它開始鬆弛下來,開始欣賞和回味它的成就,把不如意事全都擋在心外。那是如催眠般的境界,是一種自然而有的定境,這種充滿喜悅和驕傲的境界即是天道。象徵性的說法是,諸天之身,乃光所成,他們不必為塵世的俗務煩心。如果他們想做愛,只要彼此看一看,笑一笑,就夠了;如果他們思食,他們只要把心念轉向美景,就飽了。那是人類所期望的理想世界,什麼都來得容易、自然、自動;在那裡的猴子,所聞皆妙音,所見皆華美,所感皆快感。它已完成一種自我催眠,達到一種自然定境,將一切煩心或不順心的事都拋在腦後。
接著,猴子又發現它能超越天道的感官之樂及美妙事物,而進入無色界的禪定之境,或六道中最精緻之處。它知道自己能獲得純粹的精神之樂,即諸樂中最微妙、最持久者;它知道自己能以擴展牢房四壁到似乎併吞全宇宙的地步,來保持實「我」之感,從而戰勝無常和死亡。它先沉思無限空間,它注視無限空間——它在這兒,無限空間在那兒,就這樣看著。它把自己的成見加在世界上,製造出無限空間,而以此經驗安慰自己。下一步則是沉思無限意識,它不再只是沉思無限空間,同時也沉思那認知無限空間之智。如是,「我」從其總部注視無限空間和無限意識。「我」的王國全面擴展,連中央當局都想像不出其領域擴展到什麼程度。「我」 已成為一隻巨大的野獸。
「我」擴展得太大,以致「我」自己也開始弄不清其領土的邊界了。每次「我」想確定其邊界時,似乎總有部分地方漏掉。最後,「我」斷定其邊界是無法確定的。「我」的王國大得難以想像。由於它無所不包,故不能說它是此、是彼。於是「我」乃沉思非此非彼,沉思自己之無法構想或想像自己。但這種心態也終被超越;「我」領悟到這種認為自己不可思議、無法想像的觀念本身就是一種構想。於是「我」又沉思非非此和非非彼。此一無可肯定的觀念,被「我」引以為慰、引以為榮、予以認同、加以利用,從而維持「我」的續存。這是迷惑的輪迴之心所能達到的最高定境和成就。
猴子已設法達到最高的成就,但它尚未超越成就之所依——二元對立的邏輯。猴子的牢房四壁仍舊堅固,仍含細微的與己相對的「他」性。猴子可能藉著表面上與自己的投影合一,而獲致暫時的和諧、安寧及幸福;但全局是微妙的定局,是封閉的世界。猴子本身已變得像牆壁一樣的堅固,已達到「唯我獨尊」的狀態。它仍忙著自我保全和自我提升,仍陷在對世界和對自己的固定觀念,仍把第五蘊——識——的幻想當真。它的意識境界是基於定,基於對身外之「彼」的專注,所以它必須繼續不斷地檢查和保持自己的成就。「到了天界我才鬆一口氣。我終於辦到了。我如今真的把想要的拿到手了。不過等一等……我真的成功了嗎?啊!你看,對,我成功了。『我』成功了。」猴子以為它已得涅槃,其實它所獲得的只是暫時的「唯我獨尊」而已。
這種定力早晚會耗盡,那時猴子便開始驚惶失措了;它感到威脅、迷惑、易受傷害,而一頭栽進阿修羅道。但阿修羅道的焦慮和嫉妒強得讓它受不了,猴子因而變得心裡老是在盤算什麼地方出了毛病,於是它又返回人道。但人道也很苦,使得它不斷努力尋求答案,想弄清楚到底出了什麼事,出了什麼錯,結果卻只能增加它的痛苦和迷惑;於是猴子逃離了人類的思維能力所產生的猶豫不決和批評眼光,而投入畜生道。在那裡,它只是理頭挺進,不顧週遭環境,對走那些熟悉的窄路可能危及自身安全的消息,裝聾作啞。但環境所發出的消息還是突破了它的心防,使它對現狀不滿,而渴望改善。懷念天道之情變得非常強烈,使得猴子更加致力於返回天道。它幻想自己在享受天道之樂,但以幻想來滿足這種飢餓,只能讓它獲得暫時的滿足,它很快就又餓了。飢餓不斷,它終於被一餓再餓所產生的挫折感壓垮,而投入為滿足其欲所作的更加激烈的奮鬥。猴子的嗔心之強,引起週遭環境的對等反應,從而主生火爆與懼閉的氣氛——猴子發現自己又回到了地獄。至此,它已從地獄上天道,再從天道返地獄,足足兜了一圈。這種奮鬥、成就、失望、痛苦的不斷循環,好是生死輪迴。也就是二元對立的情結所造之業的連鎖反應。
猴子怎樣才能出離此一似無止境、自給自足的囚禁之環呢?有可能斷此業鏈或輪迴的是人道。人道的智力和識別力,讓人有可能對整個奮鬥過程質疑。猴子可能質疑是否非跟什麼發生關係不可,是否非得到什麼東西不可;質疑它所經歷的各種世界是否實在。要想做到這一點,猴子必須發展出全面的覺知和超然的理解。全面的覺知可讓它看見發生奮鬥的空間,從而看出其諷刺性和幽默性;它不再只是奮鬥,同時也開始體會奮鬥及奮鬥的無用。它突破過去的種種幻想。它發現不與牆壁對抗時,牆壁並不討厭,亦不堅硬,而實在是溫暖、柔軟和可穿透的。它發現它不必從五個窗口跳出,不必把四面牆壁拆掉,甚至不必考慮它們;它可以從四壁任何一處大步通過——此即為何大悲被形容成「溫柔高尚之心」。大悲是溫柔、敞開的溝通之道。
超然的理解所具有的清明和精確,讓猴子能從不同的觀點來年牆壁。它開始明白世界從未在它身外,曉得問題完全出在它自己的二元對立的心態,也就是把 「我」和「他」劃分為二的心態。它開始瞭解,是自己把牆壁弄得堅固,是它自己的野心把它囚禁起來。於是,它開始覺悟,知道若想出猶,它必須放下脫逃的野心,必須如實接受四周的牆壁。
問:如果你從未真的覺得必須奮鬥——從未到那想要離開牢房的程度——則又如何?或許你有點害怕牆外的世界,而用四壁來保護自己。
答:情形總是如此:你若能跟四壁建立友好關係,就不再有囚禁你的四壁了。你雖很想有四壁為護,四壁還是照樣消失。這是一個似非而是、充滿矛盾的情況:你越討厭牆壁,牆壁就越牢越厚;你越跟牆壁相好,牆壁就越會離你而去。
問:不知苦樂是否也像好壞、對錯那樣以智區分。這種區分是出於主觀嗎?
答:我想,苦樂出於同樣的背景。一般而言,人視苦為壞,視樂為好,以致樂被看作喜悅和幸福,而跟天道連在一起;苦則讓人聯想到地獄。因此,如果你能看出排斥痛苦以便得樂、懼受大苦而奮力求樂之中的荒謬和諷刺,你會覺得這一切都很有趣。人對苦樂的態度裡,少了一些幽默感。
問:您早些說過,我們幻想生出現象界,又想衝出現象界,我的瞭解是佛法說現象界只是空性顯現。既然如此,衝出什麼?
答:問題是在「我」眼中,現象界非常真實、難堪、堅固。現象界雖實為幻想之境,但對猴子而言,這種幻境可是十分真實和堅固的。從它迷惑的觀點來看,連思想都是非常實在和具體。只說因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幻境非有,那是不夠的。你去跟一隻神經質的猴子講講看就知道了。對猴子來說,色是堅實穩重之色。它以色為實,是因它為色所迷,不給其他看法留任何餘地。它總是在忙著鞏固自身的存在,它從不留出空隙,所以它不可能得靈悟,不可能從其他方面和不同角度去看情況。在猴子眼中,迷惑是真。你在做惡夢時,夢境是真,非常可怕;然而,你在醒後回顧那可怕的經驗時,它又似乎只是一場夢了。你不能同時採用兩種不同的邏輯。你必須看迷惑的全面,才能看破迷惑,而得見其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