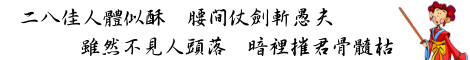死亡、責任和一個啟示
當我騎馬離開的時候,我回頭再望蔣貢康楚那間在樅樹林中的白色關房和教室——我那非常喜愛的地方;又望著那條穿過寺院的河流,與被陽光照得閃閃生光的寺院的金色屋頂,我一直回頭望到西清寺完全消失在我的視線中,才轉過頭來。
亞富噶瑪在途中興高采烈,不停地講修曼寺,說他就快與他的朋友們在那邊會面。但我和我的兩個僧人卻都很傷心,我們對西清寺有說不出的留戀。
在這次回程途中,我們遇到不少困難,馬和騾給我們很多麻煩,同行的僧人中又有人身體不適。當我們到達氏河(Dri-chu),河水正在氾濫,這條河有四百多盡寬,那只用犛牛皮製成的船,差點在河中傾覆,有一隻馬更被溺死。
修曼寺的僧人見到我們回來,覺得非常驚奇;他們雖然向我報訊,要我回修曼寺,但沒想到我這麼快就能返抵,因為我在西清寺的學習還未完成,現在既然回來,一定是我已經完成了學習,所以他們便都來向我道喜。
亞富噶瑪一聲不響,我只有告訴他們,我的學習還未完成。他們聽後很不安,攝政方丈和秘書更覺得亞富噶瑪做了錯誤的決定,因為那位年長的喇嘛已經去世,火葬儀式也已舉行,修曼寺根本就不須要我回去。
我回到寺院不久,接到一個報訊——鄰近寺院的札勒加貢仁波切(Trale Kyamgon Rinpoceh)剛剛去世,他們想請我去參與出殯儀式。這位仁波切曾在遺囑中提到要我參加他的葬禮,因為他是第十世創巴祖古的好朋友。
葬禮在創古寺(Trangu)舉行,那邊離開修曼寺的約有五里多路。在途中,我們經過了貝塘(Pelthang)機場,它是西藏人在中國共軍的指示下所興建的飛機場。
這一天,陽光普照,山谷裡一片光芒,但天空中飛機的聲響破壞了山谷的寧靜。這些飛機運用來很多供應品,因為機場還未全部完成,所以一箱一箱的物件都用降落傘空投到地面。
八蚌寺的蔣貢康楚是葬禮的主持人,他和我同時到達創古寺,我和他一同執行葬禮儀式,一直持續了兩個星期。大家都覺得八蚌寺的蔣貢康楚像有了改變,他的健康看上去似乎不大好。
葬禮完畢後,我要立刻返回修曼寺。我要離去之前,八蚌寺的蔣貢康楚對我說:「一個已經去世,另一個快要去世,這就是無常的定律。」
他斷定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會面。他用手觸我的額頭,替我加持,作同階段喇嘛傳統形式的道別。
跟著,他又給我作了另外一種加持。加持時,他的手觸及我頭上的精神穴道,他說:「這是象徵『百種姓本尊』。」
他再三強調這是我和他最後一次的見面,我請他答應讓我再和他見面,他微微一笑:「好!總之,我們會在某種情況下再會面的。」
我們啟程返回修曼寺,路經一個叫做「拜」的山谷。這個山谷很名氣,因為早在七世紀的時候,松贊剛布王〔編按:即棄宗弄贊〕派了他的公使,就在這個地方迎接他準備娶為妻子的一位中國公主〔編按:即文成公主〕。我們在山谷的岩石上,看到松贊剛布王的公使在岩石上所刻的佛教經文。這些岩石上的經文,是他在等待中國公主到達期間所刻上的,經文的文字,有些是舊西藏文,有些是梵文,這證明了松贊剛布王在未娶中國公主為妻以前,已經是一個佛教信仰者;他信仰很虔誠,曾派他的大臣森·桑布札去印度收集佛經,後來創立了一些西藏字母,專門用來把印度經文翻譯為西藏文。
據傳這位中國公主在拜谷看到了岩石上所刻的經文,她也在經文旁邊的岩石上刻了一尊二十多盡高的佛陀像,並在佛陀像的旁邊刻了八大菩薩像,和一些遠古的梵文經句。
我們在佛陀像前舉行了一個簡短的禮儀,然後繼續回程。
在我回到修曼寺三個星期以後,一個從創古寺來的報訊者通知我們,八蚌寺的蔣貢康楚已經去世,報訊者帶來一張邀請書,請我到創古寺和嘉汪仁波切一同主持葬禮。報訊者完全不知道我早已預料到蔣貢康楚會去世,對我說他去得很突然;而我清楚記得他在創古寺對我所講的話。他的死亡是整個噶舉學派的重大損失,他曾是第十世創巴祖古的弟子,噶瑪巴的老師,在這個複雜的時代,大家的確很需要像他這樣的人才,整個修曼寺都覺得很心痛,很多僧人都希望能參加他的葬禮。
我們在第二天急速啟程,日夜不歇地匆匆去到創古寺。
創古寺的僧人們在幾個星期以前失去了他們的方丈,已經非常傷痛;現在,他們又要面對另一個仁波切的死亡,使他們更加難過。
蔣貢康楚的好友心情比較平靜,告訴了我們他去世的情況。
原來蔣貢康楚忽然發病,痛苦非常;僧人們還以為他吃了不清潔的食物,一時不舒適。他被轉移到方丈的靜修室,病痛也隨之減輕,但他的身體卻變得非常虛弱。三天後,他吩咐他的侍從,說他要寫遺囑,因為他覺得這事對他的弟子們很重要。除了他的侍從之外,他不希望任何人知道他將去世,因為他不願僧人們在他面前哀傷。
他並且告訴僧人們,要他們從死亡中領悟「無常」。
為了使僧人們安心,他繼續吃藥,但是有一天,他要他的侍從在日曆上找出一個吉祥的日子。當這天來臨,一早,他就說他覺得很強壯健康,然後,把蓋著的被單拿開,盤腿而坐;立刻,他的呼吸便停止了。他就這樣保持著靜坐時的姿態,直經過二十四小時之久。
葬禮完畢以後,蔣貢康楚的遺物都被分派給他生前最接近的僧人們,我得到了他的僧袍、幾本書、一個護身盒和他的一隻小毛狗。這隻小毛狗留在我身邊,三年都沒離開,我對他非常喜愛。當我騎馬外出的時候,小毛狗總會跟隨在我的後面。
很可惜,有一天小毛狗獨自出外,竟被困在一個山撥鼠的地洞裡,走不出來。
我回到朗加哲不久,就被邀請到度魯馬拉康探訪,會計員與我一同啟程。我們在路上第一次見到共軍建築的一條公路,這條公路從中國一直伸展到拉薩。
看到它,使我覺得很驚奇——這條中國人建築的黑色公路,穿過我們的山嶽。它非常寬闊,好像山野裡的一條壕溝。
我們在公路旁趕路,公路上出現了一輛共軍軍車,車頂突出幾枝槍砲,好像一隻怪獸一樣,在公路上留下一道厚的煙塵。當軍車馳近的時候,它的巨大聲響,令平靜的山谷產生回音,我們更嗅到它噴出難聞的汽油味。
在這條公路附近居住的西藏人,已經對這習慣了,但我們的馬匹卻受了大驚。中國共軍在公路上駕駛的時候,從來都不停車讓西藏人過路,他們撞傷了很多馬匹和西藏人。
在夜間,我們見到公路上不停地出現亮得出奇的車頭燈,完全不明白車頭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會那麼亮,而當我們看到車尾亮著的紅燈時,更以為那是車在著火。
度魯馬拉康離開昌都市有六天旅程,它位於一座高山上面。高山四周是石山和湖,這個地區很寒冷。這些高原居民經營多種工業,工業中的一種是製造一些很精細的紡織品,所以他們養有很多羊和犛牛;由於這些動物須要時時轉換地點吃草,所以村民都住在能夠搬動的營帳裡面。
我們到達度魯馬拉康寺的時候,寺院已經作好了歡迎的準備。有個曾經虔誠追隨過第十世創巴祖古的家庭,送給我們牛奶和凝乳。跟著,又有一個在等待我們的僧人,送給我一條哈達,同時向我跪拜。
我們騎著馬繼續前行,遇到度魯馬拉康寺的年輕方丈亞剛祖古,他引導我們走向寺院。亞剛祖古和他的僧人也送哈達給我們,我的幾個僧人回送他們,把哈達圍在他們頸上,當我們將要到達寺院的時候,天空突然雷電大作,跟著降下冰雹。
度魯馬拉康寺的僧人和鄰近寺院的僧人們,在寺院的進口處排成兩個長行;另外,更有樂隊正在寺院的屋頂上奏樂,迎接我們入寺。
亞剛祖古手裡拿著一炷香,帶領我們進入寺院禮堂,他向我三鞠躬,然後,我們互相交換哈達。我同樣地和其他寺院的方丈交換哈達。所有僧人跟著向我獻哈達,請我替他們加持。
對年長的喇嘛,我用我的額頭輕輕接觸他們的額頭;對其他僧人,我把手放在他們的頭頂。一個僧人站在我旁邊,為我送出金剛帶,受我加持的人,每人都有一條。
加持儀式完畢以後,從修曼寺來的所有僧人,都被給予茶和飯,他們把我的茶倒進一個玉杯裡,玉杯安放在一個金屬的小架子上。我的米飯是放在一個美麗的玉碗內的,其他僧人則用陶土所制的碗。整個宴會都依照傳統,十分隆重。亞剛祖古的態度平靜保守,只是時時在微笑。我和他都知道,我們兩人的年齡彼此很接近。
度魯馬拉康在兩百多年前是一間關房,後來慢慢發展成為一間寺院。寺院裡住有很多道行高超的僧人,他們對外來的佛教老師照顧得非常周到,寺院四周住有很多閉關者,整個寺院都充滿和平神聖的氣氛,它和其他的寺院略有不同,不像其他寺院那樣刻板。
這個時候,寺院裡有一百五十多個僧人。
寺院位於山嶽中的一片平地上,在苦哈象河(Kulha Shungchu)和沙瓦奧河(Tsawa AuchuN)的交界處。寺院後面的山背後,有一間白色的關房。這間關房建立在一個山洞上,是蓮華生上師當年在西藏建立了佛教以後,用來靜坐的一個地方。
這些山嶽在遠古的時候就會被人使用過,因為山石上畫有很特別的古式圖畫。這些圖畫畫有騎在小馬上面的人群,用的是赭石顏料,上面還塗了一層似乎是滑石膠的保護物。
這一帶同時也顯示出遠古時候的佛教徒曾在附近居住過,因為這裡有一塊直立的巨石,巨石上面清楚刻有金剛空行母(Dakini)的像。
寺院前面的河對岸有一座很高的山嶽,叫做苦哈囊耶山(Kulhangang-ya),西藏遠古的「苯教」信仰者認為,這山嶽是一個非常有神力的西藏護衛神的居處,這個護衛神的配偶則住在山下一個藍綠色的大湖中。
在近苦哈山山頂處有一個山洞,洞裡的地面上有一片厚實的冰塊;亞剛祖古說他曾經爬進過這個山洞,看見厚冰下有一些很大的、似乎是人類的骨頭,但那些人骨很巨大,不可能是屬於近代人的。
苦哈山的四個山腳,建有四間和度魯馬拉康寺有聯繫的尼寺。除了參加特別的儀式以外,僧人們是不許進入尼寺的。
尼師的生活比僧人的生活更樸素,她們大部分時間都在練習靜坐,也時常幫助有病或精神痛苦的居士們。我對這些居師的精神修養很佩服。西面山腳的尼寺面對藍綠色的湖;山腳北面的尼寺近邊有一間關房,這間關房專門用來給人們實習七個星期的「中陰」冥想——「中陰」冥想是想像死亡之時和死亡之後的遭遇。
到達度魯馬拉康寺幾天以後,寺院請我主持《庫藏寶》的授課儀式。我在西清寺的時候,蔣貢康楚曾教過我《庫藏寶》。這是一個重大的工作,因為整個課程會長達六個月之久才完畢。
我的上師蔣貢康楚曾經准許我教導《庫藏寶》,但我仍舊要用幾天的時間來小心決定是否接納這個邀請。我這時年僅十四歲,我的導師噶瑪羅桑(Karma- norsang)叫我一定要仔細想清楚,究竟我能不能夠教導全篇《庫藏寶》,因為如果我在教導過程中犯了錯誤,後果會很嚴重。
很多很多人來到寺院,希望上這個課程,因此我得很快作出決定。
我用了幾天的時間來作「祈禱冥思」,希望可以從冥思中得到見解,幫助我決定,終於,我告訴噶瑪羅桑,請他通知整個寺院,說我決定接納教課的要求。
寺院上下立刻開始籌奮。他們以兩個星期的時間做成所有儀式都需要的「食子(Tormas)」——一個圓錐形的糕餅,上面裝飾著酥油雕像。這種糕餅要用很高的藝術技巧才可以做成,糕餅上的每一個形象和圖案,都像徵、蘊含著很多的意義。
我請一個僧人把所有希望上課的人的名字列出,並且一一問他們是否有接受整個課程足夠準備?
儀式正式開始,先由噶瑪羅桑念出一段評准我授課的經文,然後我才舉行授課儀式。
以下是授課儀式的整個程序:
早上二時三十分——噶瑪羅桑讀經。
四時三十分——我作授課的準備。
六時四十五分——大眾同吃早餐。
八時——我教導課程。
十時——噶瑪羅桑讀經。我作授課的準備。
十一時——我教導課程。
中午十二時——大眾同吃午飯。
一時十分——噶瑪羅桑讀經。我作授課的準備。
三時——我教導課程。
五時——噶瑪羅桑讀經。我作授課的準備。
六時——我教導課程。
八時——授課完畢。
八時三十分——傍晚的祈禱練習。
長時間的學習對大家來說,都會覺得很艱難,但一切竟然非常順利。我的導師和僧人們很替我歡喜,因為我年紀這樣輕。
他們告訴我,從今以後,我要開始專心預備擔上教師的職責。但是我自己卻認為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可以就此一直當老師;我還有很多東西沒有明白,要由我的導師給我指點。我知道,如果我自傲,那就非常危險。
我對亞剛祖古和幾位年長喇嘛說:雖然我能夠教導《庫藏寶》,也能夠舉行多種佛教儀式,但這並不表示我可以作更大規模的講座和私人靜坐指導。不過,我答應將來一定會盡力增進自己的教導能力。
六個月以後,課程完畢,我又繼續旅行,去探訪其他的寺院。
亞古寺(Yag)的方丈問我遲些可否再教導《庫藏寶》?
回程中,我們又回到度魯馬拉康寺,寺院的秘書和年長喇嘛希望我成為亞剛祖古的老師,但我告訴他們說,亞剛祖古應該去西清寺跟蔣貢康楚仁波切學習,我這時的能力仍不足夠,而且畢竟我們都是年齡相同的少年。
這時,冬天已經來臨,我們離開度魯馬拉康寺的那天,正在下大雪。寺院四周因為沒有樹,所以一片銀白,天氣非常寒冷,這個區域的西藏人常說:「這裡的寒冷,會使茶都不能煮沸。」
雖然天氣如此寒冷,寺院的僧人們仍舊替我們送行,陪我們走了一大段路程,他們都非常友善,這次道別的印象,一直留在我的心裡。
亞剛祖古和我成了好朋友,在我離去的時候,他很傷心,但我告訴他,我們很快會在西清寺再見到。我對他說:「我自己的學習還沒完成,沒有足夠的能力教導他人,如果要我做你的老師,是十分不適合的;你一定要去跟蔣貢康楚學習。」
亞剛祖古和他的僧人們陪我們走了三里路,與我們在湖邊分手道別。
度魯馬拉康附近寺院的僧人,知道我探訪度魯馬拉康寺,專程來請我也去他們的寺院,可惜我不能答應他們的要求。我唯一希望去的地方是噶瑪寺——噶瑪噶舉學派的第三重要寺院。所以在回程中便決定去噶瑪寺探訪。
環繞噶瑪寺的區域,叫做「噶瑪格魯(Karma-geru)」以藝術聞名。早在十五世紀的時候,噶瑪格魯的藝術家在西藏各處都有創作。這些藝術家的學派,叫做加比利(Gabri)學派,整個鄉村的村民都以繪畫為生。
我們到達柏亭村(Pating),這個村的村長是這一帶數一數二的藝術家。我去到他的家中,見他正在畫絲綢畫,同時在教導幾個年輕的藝術家。他的畫室放滿了大小不同的圖畫,以及不同程度未完成的圖畫。他也教他的學生用陶土塑像,教他們怎樣製造自己的畫筆,怎樣預備畫布,怎樣調顏色。他自己所畫的畫非常出名,人們對他的創作有這樣的評語:「剛布多傑所畫的宗教畫,是神聖的創作。」
在這個鄉村中,家家都有很多美麗的畫和雕刻品,每一個家庭的佛壇和寺院的佛壇完全相同,不過,村長的家特別有更多精美的圖畫,這些精美的圖畫,大多數是村長家庭多個世代所傳下來的。那些比較遠古的作品,尤其顯得完美無瑕,他家牆上還畫滿了歷史性和神話性的圖畫,絲綢畫則都是佛教性的,天花板和屋柱上畫的都是花朵和雀鳥——花朵雀鳥畫是加比利學派的特長。
在河的對岸,村民們也都從事藝術工作,但他們的創作品都是用金銀製成的。他們懂得怎樣融化金銀,怎樣鑄造金銀藝術品。村裡的一切令我又驚歎不已。我猜想,村民們的藝術技巧既然如此之高,他們的寺院裡面一定會有更多和更精采的藝術品陳列。
一條峽谷狹路直通到寺院的進口,狹路兩旁有很多岩石,這些岩石統統帶著藍色,其中一塊大岩石作九十度角地疊在另一塊大岩石上面;更高處另外又有一塊黃色的大岩石,雕刻著盤腿而坐的佛陀像,旁邊的大岩石上刻有佛教經文。
這座高山十分陡峭,岩石又那麼高,幾乎無人能夠爬到岩石上去刻畫刻字,所以這些經文佛像令我感到驚異。
岩石與岩石間有一道瀑布,瀑布上顯現出一道彩虹,彎彎地掛在瀑布高處。
走到狹路的盡頭,豁然出現了一片平地,平地上矗立著第三世大寶法王讓炯多傑(Rangjung- dorje)(一二八四∼一三三九)創立的噶瑪寺——我們的目的地。
噶瑪寺有好幾間建築物,一條河流在那幾間建築物之間蜿蜒而過。我之所以對這間寺院有興趣,是因為它有很久遠的歷史價值,它的建築和裝飾尤其特別。
這間寺院的圍牆,據說是一批來自西藏中部的泥水匠所築的,這些圍牆用很多細小的石頭砌成,別有風味。寺院的方丈最近去世,他們還沒有找到由他轉生的人,所以在我們到達的時候,寺院的攝政方丈自己引導我們進寺。
我們沿著梯級進入寺院的集會堂,這間集會堂是西藏第二大集會堂。集會堂是舉行儀式、唱經和開會議的地方。集會堂的天花板很高,有一百多根柱子支撐著它;這些柱子都採用非常非常高的樹木造成,直徑大約十六到二十尺,柱上塗滿硃砂和顏料,紅色為底,黃、藍和金色的圖案在上,看上去極其美麗。
所有建築物都用西藏獨具有建築方式建成,集會堂的窗子只讓少量光線進入,所以集會堂並不很光亮,窗子開在集會堂的高處,架在四百多枝短柱子上,這些短柱子,有一部分是用從印度運來的檀香木作為材料,十分名貴。
集會堂可通多地方,其中一個地方是方丈的住所,另外還通到十二間佛壇大殿,這些佛壇大殿專為僧人們練習靜坐之用;其中一間,裡面有很多如真人般高的雕像,那些雕像塑出了這學派的最高喇嘛噶瑪巴的多次轉生。
好幾個雕像的藝術技巧簡直盡善盡美,但是從第八世噶瑪巴的雕像起,直到再下去的幾世雕像止,就略嫌遜色。這令我心頭為之一震,使我覺得應該想法子重新復興西藏的雕塑藝術(但共軍的侵入,令我這個願望很快便成空)。
另一個佛壇大殿是圖書館,裡面有很多很多珍貴的藏書和梵文經典,這些梵文經典,有從八世紀時就傳下來的;這間圖書館被認為,是西藏第三大圖書館。它和整個寺院一樣,表達出噶瑪噶舉學派的興盛和佛教藝術的高超。
釋迦牟尼佛生前的事跡,畫滿在寺院的牆上,非常美麗壯觀,牆上也畫了噶瑪噶舉學派的歷史事跡,寺院牆前的一排架子上,放有燃著的金燈和銀燈,閃耀輝煌。集會堂的正中央有一個寶座,是用從印度一個聖地帶來的檀香木所製造的。在那深色的檀香木上,畫有很美麗的金以圖案。寶座上方掛著一條金色錦鍛,四周圍著一條白色哈達;整個寶座都刻著獅子圖案。寶座座位的墊子上,蓋著一塊以前中國皇帝送給噶瑪巴的絲緞。
集會堂的盡處通向另一間大堂,大堂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供奉過去世的佛陀塑像;第二部分,供奉現在世的佛陀塑像;第三部分,供奉未來世的佛陀塑像。這些塑像非常巨大,眼和眼中間的位置就有五盡多闊,釋迦牟尼是現在世佛陀,塑像用銅和金造成,肢體、手、腳等部位都先分別鑄造,然後再熔接在一起。佛陀的頭部非常精緻,額頭中央鑲有一顆巨大的金剛鑽,傳說這顆巨大的金剛鑽是來自天鷹加魯達的口中。這塑像是由第八世噶瑪巴(一五0七∼一五五四)所設計,他的藝術造詣極高,大堂裡的一個獅子寶座,上面的雕刻就是他的傑作。
過去世和未來世的佛陀塑像用陶土和神聖草藥混合製成,這兩個塑像上都飾有很多珍貴的寶石,塑像的額頭中央則鑲有一顆名貴的紅寶石。
三尊佛像前面各放一張台子,讓人們放置奉獻物品。
寺院的外表也十分壯觀,極天然和人工之美,它的後面是高高的山嶽,中間有一條河流,河水流動得很快。寺院的屋頂上有一座金色的「寶頂」(Serto)(是象徵聖嚴的屋頂裝飾。這種頂飾,在西藏很多寺院的屋頂上都有,它甚至被裝飾在馬匹的頭頂,表示騎馬的人是重要人物),有一條金色的鏈,鏈上掛著鈴,從 「寶頂」上面垂到屋頂上面。寺院的屋角還有較大的鈴。寺院的小石牆上有一些木刻的獅子,寺院的屋頂鑲金,不論晴雨都燦爛有光,遠遠就吸引人的視線。
噶瑪寺的高超藝術,主要出自第七世、第九世和第十世噶瑪巴。這幾個轉世喇嘛,個個都是藝術高超的雕刻家、塑像家和畫家,他們還懂得刺繡、融金和鑄造金、銅、鐵像。這幾位噶瑪巴的藝術家,的確是西藏罕有的、數一數二的,他們也可以說是西藏藝術的代表者。而在這幾位喇嘛在世的時期,西藏的神聖佛教學說也進展得很蓬勃,他們的著作尤其重要,把玄學和思想合而為一,對佛教作出重大的貢獻。
寺院對面的小山上建有一間關房,關房前面是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路,小路旁有一叢檉柳,修剪成西藏字噶瑪的「噶」字形,十分別緻。
我們離開噶瑪寺後,我一連又接到很多的邀請書,但是,因為在每年的最後十二天,修曼寺要舉行一連串特別的祈禱儀式,所以我只好拒絕了那些邀請。
這種年終的祈禱儀式,一向被認為非常重要,不過我在十一歲以後,一直都在別處,不在修曼寺內,所以錯過了幾次參加這種祈禱儀式的機會。
它是慶祝「上樂金剛(Khorlo-demchog)」和「四臂大黑天(Gonpo Chashipa)」的儀式。儀式包括靜坐和誦經。誦經時,鼓和鐃聲伴隨,唱經將完時,喇叭樂聲也加入。
僧人們在法會舉行的時候,整天不可以休息,晚上也只能睡四個小時。
年終法會的作用,在於驅走邪惡,增強下一年的聖靈力量。我以前也曾參加過三次,第一次我還年幼,只准在日間作旁觀;其餘兩次,我雖然能夠參加,但是覺得儀式實在很長很累人。
今年完全不同,我已經十四歲大,而且對儀式有了理解,所以能夠很愉快地完全投入。
十二天法會完畢以後,我去到多傑昆宗,和那裡的閉關者一起過新春,離開了修曼寺的忙碌活動。我希望新春過後,能夠早日再去西清寺,繼續我的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