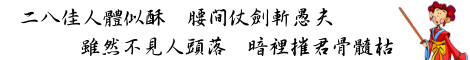多天的危機
我決定如果嚮導和他的妻子在下午二時再不來,我們便自己啟程——他們果然仍沒有出現,我們於是走上積雪的山路。這天天氣十分晴朗,雖然身在高山,但仍然可以見到涅沃附近的山嶽。我第一次感覺到我們走的路線是正確的,而且一定會抵達印度。我感到有一種力量在指導我,覺得我並不是獨自一個人在經歷這個路程。
我們在寒冷的天氣裡走了一天,當我查看同行的幾組人時,發覺他們吃的食物太多,於是我認真地對他們解釋,我們帶來的食物是要維持很長時間內,這樣才有機會生存;同時,又叫他們小心,不可以在空曠的地方生火,以免被共軍飛機偵察到;而且以後甚至不可以再生火,如果有人要生火,一定要先得到我的同意。
我對他們說:「我們去印度的路程,要把它看作是朝聖的旅行,西藏人以前很少做成功這件事。不論現在印度有沒有改變,佛陀對印度的神聖加被仍會保存。印度是佛陀釋迦牟尼佛生長、悟道、說法和涅槃的地方,有著永恆的價值。我們都很幸運,因為我們的路程比以往的朝聖者的路程更困難,這表示我們會學到更多的東西、得到更多的啟發。我們不應該只想著外界敵人的力量,每一個時刻都應該提防自己內在那股消極的摧毀力量。如果不好好行事,就污辱了我們的神聖旅程,我們踏在路上的每一步,都是神聖和寶貴的。」
我說了這一番話以後,大家又等待嚮導的來臨,但仍然沒有他的蹤影,因為我決定不再等待,繼續前進,好在天氣很晴朗。
沒想到就在這個晚上,嚮導和他的妻子忽然到來,身穿剛保地方的衣服。我曾叫他多帶一些剛保的衣服來,但他沒有做到。
嚮導的名字叫哲巴(Tsepa),他是一個很好的人,而且很明智,最重要的是他曾遊歷過我們要去的地方,對那裡的地形非常熟識。他向我們道歉未能在約定的日子到來,因為他忙於賣掉他的東西,只帶來了一枝槍和一些軍火。我向他解釋我們要走的路線是一些村民提議的,他同意村民的意見,認為這條路可以走,而且肯定我們大有機會由此路通往印度。
第二天清早,我們便在雪中趕路,我們發覺原來山脈並沒有預料中那麼陡,新下的雪凝結成冰,使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在上面步行。當我們來到山頂的時候,大家依著西藏的傳統,大叫「樂逸(Lhagyalo)」——勝利之神。
我們現在面對印度,前面是唐基谷,谷中似乎並沒有人,但我們仍舊擔心,怕有共軍埋伏在那裡。我們一夥人所穿的深色衣服在雪地上非常明顯突出,我希望共軍在我們過山的時候不會發覺我們,我請他們盡量避免發出聲響。
大風刮在我們的臉上,天氣非常寒冷,太陽似乎沒有供給我們溫暖。我派了一些人前去探路,看看是否可以繼續走過山谷,再過一個山脈,去到剛保低地。當他們去了以後,我們在山腳休息。他們回來告訴大家,路上沒有見到共軍,但雪地上有些西藏人的腳印,不過那不是新的腳印。
一連幾天,我們都走在山谷的平路上,非常輕鬆,但大家都不放心,怕行蹤被共軍發覺。夜間,我們到牧人留下的草屋休息,因為這裡的高原樹木很少,但有很多草地,所以牧人在夏天常帶他們的動物來這裡吃草。
現在是九月底,地上生長很多野莓,可以採來吃。我們走下山谷的斜坡,來到一個有很多樅樹的地方,見到地上有些新的腳印,大家立刻停了下來。
我派嚮導哲巴假裝是一個報訊者,去前面的鄉村查探,村民給他很多關於共軍的消息。
據說有很多共軍在剛保低地嚴密地守衛著。村民們雖然仍舊能夠在附近和其他村民交換米麥,但是因為共軍的侵入,使他們都非常慌亂。村裡較富有,能夠請僕人做工的家庭,尤其受到共軍的折磨,共軍命令僕人穿上主人的衣服,強逼主人換上僕人的衣服。共軍要被捉的西藏人幫他們建築公路,很多西藏人都因此餓死或過勞而死,所以村裡的氣氛充滿恐怖。
哲巴從村民口中得知更多關於這附近的地理形勢,和向他們請教我們應該走哪一條路,他更買到少量額外的食物。
我又派人向會計員的一夥人和亞剛祖古報訊我們在哪裡,以及準備以哪一條路線逃走。
我們走下山谷,來到一個湖邊。這裡的風景實有幽美,所以我們都不再理會將發生什麼危險就選了這地方休息,但天氣卻越來越寒冷。
第二天的路程全是上山,慢慢來到較少樹木和很多岩石的地方,山谷也開始越來越狹窄,前面好像有些鄉村。
一天早上,我們聽到人聲,有幾個人便拿著槍枝去到那座剛剛越過的橋上看望,發覺原來是我的會計員和一個僧人正在向這裡走來。
他們說亞剛祖古等人在後面,不久就會跟著到來。他們已經賣掉大部分的東西,但是有一百二十多個難民加入了他們,堅決要跟著亞剛祖古走。會計員說所有的人都想跟我們在一起。
他同意我的計劃,認為我選擇了正確的路線。但他又說,在印度那邊的人正在組織拯救隊,為過境的人接應,他說最好我們能夠等候拯救隊的組織工作完成以後才繼續前進;但我決定繼續前行,因為天氣還算不錯。
山谷的路程比預料的要長得多,所以我們在途中又找牧人的草屋休息,在裡面好生火取暖、燒煮食物。
第二天一早,我們便嘗試越過高山,但只走了四分之一的路程便開始下雪,而且風雪大得我們只好停止前進。好在我們又找到了另外幾間草屋,在裡面停留了一日一夜。
到了下午,有些人掙扎上山,試試他們可以走多遠。他們回來報告說,山上的雪非常的深,比綽普的積雪還深得多。我安排了八個最強壯的人把行李轉給其他人,先去山上,在雪中開路,使大家可以跟著前進。
結果,他們發覺不可能在厚雪中行走,只可以俯臥著,用身體的重量把雪壓實;同時這種方式非常困難,一個人臥下壓雪五次,就會筋疲力盡。
我們在一個人接一個人的輪流壓雪中前進,前面山非常陡,使我們無法壓成一條鋸齒形的路,所以幾乎要掉頭退回。但我們還是奮力上山,到達了山頂。遠遠的,望見山谷下面好像有一夥人跟來,便以為那當然是亞剛祖古和與他同行的一群。
我們來到另一個高原,那時已是下午時分。我們發覺四周都是岩石,在越過岩石以後,竟突然發現來到另外一座更陡峻的高山。因為這個高山的高度,使得地上的雪比較堅硬,所以走路便稍微容易一些。
領導我們上山的人很難一下走在可以通行的路上,所以有時候大家都要掉頭再走,摸索另一條路,多花很多時間與精力。最後,我們終於見到祈禱旗插在山上,這表示我們已經又來到一個山頂。那時太陽也下山了,天空只剩下一片紅光,風刮在我們臉上,十分寒冷和刺痛。
從這山上望下去,因為下面有很多岩石,所以不能看清楚下面的實況,山谷好像沒有人。我們一夥人中,有些人走得很慢,離開我們很遠,還未來到山頂。
我擔心年老的人,深怕他們無法在雪上過夜。我知道他們沒有能力更快地上山,能夠跟隨在後已經是奇跡了。我們查看名單,肯定羅年輕的人會照顧他們的父母。
所有已經來到山頂的人,在黃昏的時候又開始下山。我們見到下面遠處有一條很長的好路,但是要到那裡卻很艱難,因為附近有很多突出的巨石阻擋著去路。當很多石頭滑下山時,我們要向下面的人大聲警告。
大家都分散開了,唯有靠自己想辦法下山。到了天黑的時候,各組的領導人都陸續來到可以過夜的一片山地上。這裡有一塊大石頂部向下彎,一部分的人可以在大石下面休息,避開風雪。他們都堅決要我在大石下面過夜。很多人都被迫躺在雪地上過夜。
天亮以後,我和各組組長一同去視察每一個同行者,因為怕年紀大的人會身體不適,或遭遇到什麼意外?當我們發覺每一個人都仍很健康的時候,非常高興。大家集合之後,便繼續下山,雖然大家因為前一日旅程的艱難仍舊非常疲乏,但都願意掙扎前進,因為糧食和時間已經無多。
我派了一個人先下山去查看山路前面有沒有障礙?他回來說,前面一路通順,沒有見到任何人或野獸,這時大風停止了,太陽在天空高高的照耀著。
過了這個山以後,我們就離開了唐基谷,到達一個高原,高原上有一條大溪,是很多小溪的合流。我們的嚮導哲巴指引我們沿著其中一個山谷走向東南方。那山谷兩旁佈滿很多高山,我們只能走在山谷底,直到找到轉角。
有一天,我們正在慢步前旱,亞剛祖古突然從後面大步追了上來,他是一個人先趕來加入我們的。我們兩人得以重聚,都非常高興。
他說,因為我們已經先開了路,所以他們走時並沒有什麼大困難。他的一夥人跟著到來,我們大家就一起去牧人的草屋休息談話。
亞剛對我說了很多的話,當他接到我的報訊,說我賣了所有動物準備離開涅沃步行去力岡卡時,他的兄弟和會計員都作了異議;他們認為一定有辦法可以騎馬去力岡卡,並帶著馱載行李的騾子和犛牛。後來他們成功地過了亞拉度河,經過一條抵抗軍建造的臨時橋樑,向東南方進發,接著,又改變方向,打算越過很多高山去力岡卡。
他們走的山路時常中斷,要用樹幹架在岩石上才能走過去。有一次還要自己造橋,這些困難的工作都由強壯的男人擔任,其餘的人看管著動物在一旁等待,大大地拖延了行程時間。
雖然他們都很小心地看管動物,但有三匹馬在過橋的時候跌死了;又因為沒有足夠的營養和充足的食物,所有的動物都很虛弱,有些甚至虛弱得不能繼續前進,只能把它們送回積米仁波切那裡休養。
他們一夥人終於到達力岡卡,一共帶有三百多隻犛牛和二十匹馬,使力岡卡的村民都很驚奇,因為他們從來都沒有見過犛牛和馬。為了那裡沒有足夠的草地供給動物吃草,所以要用殼物糧食餵它們。
當會計員哲塞知道我們在一星期前便已離開力岡卡前往綽普谷時,他就把他的動物托給一些村民去照顧,不再帶著它們。有些難民不忍留下他們的動物,啟程時,仍舊帶著動物前往,他們以為它們可以游泳過河,但是在過河的時候,河水非常洶湧,大部分動物終於都被大水沖走。
亞剛祖古和會計員等人去到綽普谷,那時我們走過的路已無足跡,有些難民害怕找不到我們,所以帶了剩下的動物回去山谷。
亞剛祖古和會計員堅決繼續往前走,在途中意外地找到了積諾祖古,發覺他病得很重,積諾祖古告訴他們,自從離開我們以後,覺得非常孤寂,但因為我們繼續前往印度,又使他替我們高興,認為雖然我們在途中會有危險艱難,但是他全力贊同去印度的計劃。
亞剛祖古來到後的第二天早上,我見到很多很多人來了,原來是會計員一夥人,有一百二十多名,加上我們一百七十多個,總共大約有三百之多。當我們一齊啟程時,看上去真像一支軍隊,不太像一群難民。
我們走的路仍然有很多岩石,而且要經常攀越很陡峻的山坡,不過我們終於來到兩個山谷的交界處,河邊就是從涅沃山谷通往剛保的貿易大道。
我們的偵察者說,他見到一個帶著四隻犛牛的人在路上走,為了怕是間諜,所以我們都停下來,躲在大石堆後面差不多有兩小時,直到我們中的兩個人爬上石山,眺望道路兩面約三里遠的地方,都看不見有人在附近時,大家才越過道路,立刻涉水過河。
過河後,來到一個狹小的山谷,在山谷裡找到幾間牧人的草屋,但那裡卻一個人也沒有。
這一晚,我們睡得很不安寧,很多人在半夜以為聽到有人來而吵醒了大家;新加入的人當中又有很多嬰孩,整晚都有嬰孩的哭聲。
天亮以後,哲巴和我商談計劃。他說他認得我們過夜的地方,現在應該離開這個山谷,越過一座高山,向南方前進;雖然高山的另一面是什麼地方他不能肯定,但肯定方向絕對正確,我們會更加接近剛保。
沒有其他人清楚知道我們究竟在哪裡?所以大家只能把信心放在嚮導的身上,願意跟隨嚮導走。我提醒大家要盡量避免冒險,避免走空曠的山谷,因為現在人多,走在空曠的地方很容易被發現,同時,大家還要盡量壓低聲音。
沒有多少人知道在危急的關頭應該怎樣躲避,很多人身上都穿著顏色鮮艷的衣服,連在夜間都很容易被見到。他們一心倚賴領導的人,卻不肯運用自己的思考力,更不知道共軍隨時可能會出現把大家捉住。
我們現在決定走的這條路,對年老幼和年幼的人來說會很困難,但是沒有其他的路可以選擇。
啟程之前,我叫大家集合在一起,特別向他們解釋說:「現在,我們就快進入更危險的地帶了,因為,在這些地方有很多居民受共軍所控制,大家不可以信任任何村民。只要有人去和村民打交道,他們一定會發現我們是難民,我們更絕對不能對任何人洩漏計劃。買東西一定要付錢,遇到村民或任何陌生人都要對他們有禮貌。最重要的是,應該盡量少發聲音。如果一旦有人生病,應該立刻來通知我。」
我們仍舊能在白天趕路,登上一座高山。嚮導肯定很快便會見到剛保低地。我們個個都很興奮,但當我們來到山頂的時候,卻只見到更多的山,附近完全沒有人煙。
嚮導哲巴一時也覺得非常困惑,想不出究竟應該怎麼樣走?但他終於想清楚,指示大家走向下面一個山谷。不過,在我們到達下面那個山谷時,卻發覺並沒有什麼通路,於是,又要轉去另一座山;而在過了那一座山以後,發現原來我們還要再過第三重山。
上到第三重山,來到一個陡峻的懸崖,山坡上長滿滑腳的短草,下山非常危險,有些老人在下山的時候滑倒。不料下了山之後,又面臨一連串的高山,只有跟著野獸留下的足跡迂迴而上。當我們走到另一座山的山頂時,總算見到有一片圓圓的凹地,長了很多樹木,可以容納我們休息、過夜。
我們的嚮導知道他自己都迷了途,感到非常憂慮。會計員更是非常煩躁,埋怨沒有一個人知道正確的路線,他說他可以肯定,其他的難民現在一定已經被抵抗軍拯救隊救了。我對他說,我們完全不能證明是否有拯救隊在救難民,現在大家都該信賴我的領導,每一個人都要盡力為大家設想。
第二天早上,我們沿著一條窄小的山路往前走,山路斜度不高,走起來不太費力,不過這一帶沒有樹木,我怕有人會見到我們。
在快接近黃昏的時候,我們見到有些小石山,小石山前面又有幾座高山,山頂被白雪掩蓋。我們都不知道那邊是什麼地方?有人認為它是剛保高地,另一些人又認為它是剛保低地。
我們繼續上山,山上的積雪和正在下山的太陽互相輝映,看上去好像是堅固的金屬一樣;我們怕如果再走上去便會去得更高,不適宜過夜,所以在途中就停下來,雪很厚很多,附近沒有溪流,唯一的水源便是地上的積雪。為了怕火被共軍見到,我們要限制生火,而事實上也很難找到可以燃燒的東西。
第二天,我們發覺走的方向錯誤,於是改變方向。
才走下另一個方向的下一個斜坡,前面就出現一個溫暖的鄉村,有一條河在村中穿過。不過,好些人遠遠見到河邊有一團漆黑的東西在動,以為是埋伏的共軍,都驚慌萬分,有些人還說他們聽到聲音,因此很多人都慌作一團。
我用望遠鏡望向河邊,見到那在動的東西原來只是一隻年幼的犛牛,不過,也可能有一個牧人就在它後邊。後正我們無可選擇,因為如果停留在斜坡上,就會更加引人注目,所以只有繼續走下山坡。
我們通過了一些矮楊柳樹,找到一間空草屋。一小部分的人進去草屋過夜,其餘的人就躺在空曠的地上睡覺。部分年輕人組織了偵察隊,在夜間四面查探,結果認為附近都沒有人。
有些難民已經非常缺乏糧食,他們來問我幾時可以再補充得到糧食?我對他們解釋,在短期內,不會有增添到糧食的可能,叫他們一定要非常小心分配所剩餘的東西來吃,以免半途食物中斷。
過了一個星期,他們又來到我面前,問我有沒有額外的糧食可以供應他們?可惜我們自己的糧食也僅僅只是勉強夠吃,實在無法使他們如願。更由於我們每天只走短的路程,所以糧食消耗更多,需要量也更多。
現在,我們的嚮導完全不知道究竟身在何處?因此只有盲目地繼續向前行,過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山以後,才來到一個很低很大的山谷,這個山谷看上去似乎有人居住,所以,我和亞剛祖古、亞古祖古、容登、嚮導,決定先向前走,打探情形。當我們知道山谷裡原來並沒有人時,大家都很放心。但隨後卻發現一些人的足跡和糞便,容登和嚮導都認為那些足跡大約是在二十四小時之前留下的。
我們幾個人商量下一步的計劃,但沒有一個人能夠作出肯定的主張。
眾人都在等候盼望我們。很多人更想能停下來煮茶喝,但我認為這會有危險,所以叫大家動身走下山谷。
走了半程,見到一座高山,山坡上密密的長滿了松樹。我突然感到我們走的是正確的方向,但會計員卻不同意,他認為向前碰運氣的走法不切實際。在我們已經登上山坡大約走了一里山路的時候,會計員又和其他幾個人提議說應該走山谷,不應該登上山坡。他們埋怨沒有機會喝茶,又非常疲倦,還要他們掙扎上山。
我向大家解釋:如果我們繼續沿著山谷走,就會偏離去印度的方向,而且山谷附近很明顯會有人居住。
會計員和另外幾個人顯得很煩躁,開始和我辯論,我只有對他們說:「如果你們想繼續沿著山谷走,悉聽尊便,但我對你們以後不再負責。我自己決定上山,等找到比較荒蕪的地方,自然會停下來,大家煮茶喝。」
有些難民大聲嚷:「對!這是正確的做法。」最後,大家——包括會計員等人在內——都決定跟我上山。我很明白人人都非常疲倦,但我對這條路很有信心,覺得一定不能改變。
至於我自己,在這種山野環境裡走路,竟會帶給我很多精力,我的體內似乎有一種力量在推著我前進。
我們繼續登山,越過松樹林,來到一處有很多矮樹叢的地方,這些矮樹叢常使我們走錯路。我們要推開它才能前進,有些持劍的人便一面走一面斫樹。最後,總算大家都穿過了矮樹叢,來到一個滿佈岩石的山坡。
在山坡上,我們聽到遠處傳來聲響,好像是爆炸聲,又好像是貨車行馳聲,有些人認為那是戰鬥的聲音。
我們又走了一程,到達一個乾涸的山谷。山谷裡有三條通路,大家不知道應該應該選哪一條路走?由於現在完全要我一個人作出主張,所以我們的嚮導也轉過來問我怎麼走?
我說:「走中間那條。」
嚮導問我為什麼這樣選擇?我回答:「總要選一條路。」
我又引用兩句西藏諺語:「疑心不能使人滿願。」「兩根針在一起,不能同時縫東西。」
我們穿過中間這條通路,向前面進發,我見到路旁有一個紀念石碑,覺得很高興,這證明從前有人走過這條路。
我們又走了一大段路,來到一個峭壁,下面是一個湖,湖水照映著黑色和紅色的石頭。我仍舊堅定地相信我沒有走錯路,我們應該走這條路。於是,大家一起爬過一塊又一塊的大石,來到一處有野獸足跡的山野,然後決定在這裡過夜。
我們在此生火,為了遮掩火光,使盡一切辦法都功敗垂成,而天空卻飛過一架飛機。
此時,我又接到另外一則壞消息:有一個老人覺得非常衰弱,由家人扶著他走,其他人則幫助他背行李。
第二天,我們見到湖另一邊的山野很平、很空曠,但再走下去,又有幾座高山,大家又要艱苦地爬山,跟著動物的足跡走。這裡的積雪較深,我們要請八個壯男再作臥地壓雪,為大家開路。僥倖這裡的山坡沒有上次的陡,所以比較容易上去。
來到山上,哲巴忽然覺得形勢似乎有希望,我們再次見到南面好像是雅魯藏布江。
但目前的處境並不輕鬆,一重又一重的高山等著我們去征服。八個壯男輪流著,一次又一次地躺下壓雪,然後,又是一座很陡峻的高山在等我們去爬,使我非常為那位衰弱的老人擔心,雖然糧食已經剩餘得很多,我們還是決定給他多吃些食物。他吃了食物之後,情況稍微好轉,可以繼續前進。
我們的嚮導現在非常肯定所走的方向是正確的,所以我很高興,希望快快登上這座高山,但當我們到了這座山的山頂以後,卻見前面又是更多的高山,一重一重,而且山頂都積了厚雪。不過,早些時聽到像爆炸又像貨車的聲音,現在已經聽不到了。
終於,我們似乎走到山脈的盡頭,前面有幾個湖,而且有些平地。
我們在一個湖的旁邊停下來休息,我用望遠鏡觀察前面的山谷,見到山谷很寬闊,山谷裡有一條河,還有草原和松樹叢,沒見到任何人在山谷裡出現。
嚮導認為我們大概在哲拉宗(Tsela Dzong)附近,位於剛何河上游和雅魯藏布江的交界處。
我知道這一帶會有危險,尤其如果走錯了路——因為這區域有很多人居住,而且普遍受共軍的控制,我們曾聽說過共軍在這一帶向村民灌輸共產主義思想,這表示我們以後不可以再信任村民,有些村民可能已經成了共軍的間諜。
我向大家請教,他們都一致同意,認為如果我們的確接近哲拉宗的話,將可能遇到危險,所以最好能夠轉走東方,走向剛保低地去。
大家決定再向山上走一程後,便向東南方前進。這條向東南方向的路線很長,路上又有很多矮樹叢。我們走了一大段路後,來到一排山谷前,又花一個星期的時間上山、下山,才來到較平坦的山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