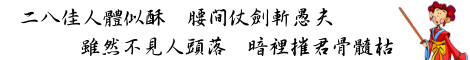|
| 首頁 → 佛教圖書館 → 基礎佛理 |
| 閱讀文章 |
學佛知津 聖嚴法師著太虛大師評傳
附錄:太虛大師評傳 寫作的動機 太虛大師對於近代中國佛教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但是,真正瞭解太虛大師的人,那就很少了,至於繼承太虛大師的思想和事業者,幾乎已經沒有這樣的人了。太虛大師,出現於世,頗像太空的慧星,出現之時,光芒萬丈,消失之後,竟又寂寂寞寞了。所不同的,太虛大師為我們留下了一部達七百萬言的全書,這是他的法身舍利,可以供作後人的研究參考。這該感謝太虛大師,也該感謝全書的編校者印順法師及續明法師等的辛勞。 我對太虛大師的思想與事業,認識得實在太少,從學脈的系統上說,或可沾到幾分「再傳」的光榮,因在我的師長之中,有幾位是出於太虛大師的門下;然從思想及事業上說,我的師長一輩,也無有一人是走太虛大師的路線。 正因如此,當我南來靜修之際,有些師友給我提供學行路向的意見;當我要掩關了,又有一些好心的師友,給我提示勖勉,並且提到了古代及近代許多大德先賢的名字,要我學習他們,向他們之中的某一人看齊。但我本人,除了學佛,誰也不想學,如要東施效顰似地學這位大德或學那位大德,終究是學不成功!太虛大師便說過:「不能倣傚的,倣傚我的人,決定要畫虎不成反類犬。」人各有其高低與輕重不等的根機或資秉,人只能使自己學成聖賢,絕不可能學成相同於他人的聖賢,除非是成了佛,即使是佛與佛的福德智慧,是平等的,但也不是一樣的。故在古聖先賢之中,相近的當然有,相同的則絕對沒有。 不過,古聖先賢的行誼,均足供後人的傚法和參考。所以我在修習之中,仍以古聖賢的行誼,作為借鏡。 近代,有人將太虛、印光、弘一、虛雲四位大德,與明末的蓮池、紫柏、憨山、澫益四位大德,相提並論,並許為兩個時代的八位大師,因此我對這八位大師的著述,均約略看了一些,到現在為止,比較地說,我受澫益與弘一兩位大師的影響稍微多一些。太虛大師的著述,我看的比較多,所受的啟發很多,但我無法學成太虛大師,這是個人氣質的問題,不是太虛大師的思想不配我接受。 正因如此,我對太虛大師的思想,總是未能認清;我也相信,今日的佛教界中,真能認清太虛思想的人,不會多。即使一些時常運用太虛論證,來發表他們自己意見的人,也少有真對太虛思想下過深入的工夫。 今天,最能明白太虛思想的人,要推印順法師,他是太虛大師的門下,也是太虛全書的主編人,但其思想,卻與太虛大師有所不同;一些太虛語句的習用者,卻又不是太虛思想的真正瞭解者,更說不上是太虛思想的繼承者或發揚者。太虛大師出現於人間,在人間發光發熱,人間對於太虛大師,竟是如此的冷漠! 我不算是瞭解太虛大師的人,但是,當我讀完「太虛大師年譜」之後,總覺得有許多話要說,並且縈迴腦際,久久不去。所以,這篇文字,實也只是其「年譜」的讀後感而已。 「太虛大師年譜」,是由印順法師編述的,故從年譜之中,不但看到了太虛大師的崇高偉大,同時也看到了印順法師的治學精神。這使我感到,太虛大師長於恢宏廣博,印順法師優於縝密專精。他們二人的性格不同,所以思想意趣,也互有異。 最先,當我看過太虛大師的自傳以後,總以為年譜與自傳出入無幾,同時我也知道,印順法師與太虛大師的思想,互有出入,以印順法師編述太虛年譜,可能難保持平客觀的態度,所以一直沒有看它。想不到當我看完年譜,除對太虛大師更加瞭解與更加崇仰之外,對於印順法師竟也肅然起敬了。在年譜之中,雖也加入了編述者的意見與評斷,但那只有增加年譜的光彩,並無損於大師的崇高偉大。尤其是對年月日期的考核,以及年譜素材的取捨抉擇,精審縝密,大有史家的風骨。不誇、不褒、不隱、不貶,純以平實的手法,介紹太虛大師的一生,字字有根據,事事有出處。我讀了很多年譜,這一部年譜的寫作法,最能使我心折。 這是一部行誼年譜,也是一部學術年譜,其中介紹太虛大師的一生行蹤,但也扼要而有條理地介紹了太虛大師的思想。故我現在要介紹太虛大師,就得略介這部年譜的內容。 大師的一生 縱觀太虛大師的一生,正如李白的詩境:「黃河之水天上來」,但又「奔流到海不復回」!他像是天縱的聖賢,不假造作,便能救人救世;又像是香象渡河,迅速地度過了他偉大的一生,又去得無影無蹤了。 出世未久,父喪母嫁,等如孤兒,而與外祖母相依為命。自五歲開始,隨其次舅讀書,九歲之後,便隨其外祖母到處游散,即在九歲以前,也因體弱多病,而致時學時輟,到十三歲便去當百貨店的學徒,十四歲時,竟然已有文思,而學著作文了。十五歲時又因體弱而離開了百貨店,由於外祖母有虔誠的宗教信仰,引使他在十六歲的那年,因為慕習神通而出了家。十八歲時便在天童寺得到圓瑛法師的器識,訂盟為兄弟,當時的圓瑛法師,已是二十九歲的人了。十九歲由圓瑛法師介紹至慈溪汶溪的西方寺閱大藏經,當其將大般若經快要讀完的時候,有一天竟在看經之際:「忽然失卻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靈光湛湛,無數塵剎煥然炳現,如凌虛影像,明照無邊。座經數小時,如彈指頃;歷好多日,身心猶在輕清安悅中。」他是得到悟境了。自此以後,文思活躍,所學的佛學與世學,也均能隨心活用了。 二十一歲至南京楊仁山居士所辦的祗洹精舍求學,故與仁山、智光、梅光羲、歐陽竟無等,均有同學之誼;二十二歲又從西方寺去廣州參加了革命運動、並主張佛教應該要變,非變不足以通其時代。是年,又在廣州的雙溪寺初任住持;二十三歲時,因逢廣州革命失敗,而作「吊黃花崗」的詩篇。同年五月,因避清廷捕捉黨人之風險,回到浙江,又至普陀山度夏,印光大師閱其詩文,即深為讚許。二十四歲,因受革命思潮的影響,在鎮江金山寺,開佛教協進會成立會,而遭舊派反對,致有「大鬧金山」的事件發生,但那完全失敗了。 二十五歲,太虛大師的戒和尚寄禪長老入寂了,寄老是其唯一心折敬仰的大德,寄老對於太虛大師,也寄望甚殷。故此對於太虛大師,是一大哀痛!當年,擔任佛教月報總編輯,是其從事佛教文化工作之始。首先提倡中國佛教教產的法派傳承與剃度傳承的改革,而主張寺產為僧眾公有。對於僧裝,也首次提出改良的意見:「除袈裟直裰之禮服外,他項似不妨隨俗。」 二十六歲時,由於他的抱負未能實現,自大鬧金山之後,對於佛教,頗抱悲觀,故藉泛覽新舊文學,以自消遣,多與文人往返,習近文人。但至此時,竟又捲於塵俗生活而回俗趣真了。故至此年十月,即在普陀山掩關了,是由印光大師為其封關的。是年冬,有「一夜,在聞前寺開大靜的一聲鐘下,忽然心斷。再覺,則見光明無際。從泯無內外能所中,漸現能所內外,遠近久暫,回復根身座捨的原狀。……心空際斷,心再覺漸現,符起信、楞嚴所說。」這是又一次的悟境,同時,也就從此而宗於起信論與楞嚴經了。二十七歲,在關中著作「佛法導論」,是其有系統的著作之始。由其所讀經論的影響,故主張:「整僧之在律,而攝化學者世間需以法相。」這是他後來整僧及化世思想的基本觀念。同時見到革命建國的形勢及需要之後,編著了一部「整理僧伽制度論」,期能健全中國的佛教,但他失敗了!但對僧裝問題,又主張「袍衫如舊」,而傾向於保守了。 二十八歲,作成「首楞嚴經攝論」,本楞嚴經義,以總持大乘,得中國佛學的綱要,這也是他當時佛學思想的結晶。同時就在這年,對於唯識義,又有所悟,他說:「曾於閱述記至釋『假智詮不得自相』一章,朗然玄語,冥會諸法離言自相,真覺無量情器一一塵根識法,皆別別徹見始終條理,精微嚴密,森然秩然,有萬非昔悟的空靈幻化堪及者。」這是第三次悟境,而且比前二次更勝了。由於悟境的關係,他的一生,論理境時,皆不出起信、楞嚴、唯識的應合與開發了。但其所講唯識乃以起信論和會,與專宗唯識者有所不同。 二十九歲二月間出關了,十月間即代圓瑛法師應台灣基隆靈泉寺之請,到了台灣,參加法會,講「真常的人生」及「佛法兩大要素」。十二月二日即由靈泉寺住持善慧法師陪游日本。十二月十五日即離開日本,這是太虛大師初次出國。 三十歲,集東遊的詩文、遊記,編成「東瀛采真錄」,轉交台灣靈泉寺印行。當時的他,「曾有撥一代之亂而致全世界於治的雄圖,期以人的菩薩心行——無我大悲六度十善——造成人間淨土。」這是多麼豪壯的志氣。 三十一歲,那是民國八年,北京大學發動了「五四運動」。曾與出佛入儒的梁漱溟以及北京的幾位名學者晤談,並告知胡適之,宋明儒家的語錄體,是創自唐之禪宗。十一月,應南通張季直請,講普門品於狼山觀音院。十二月,改「覺書」季刊為「海潮音」月刊。卓錫西湖,專心編輯。 三十二歲,與歐陽竟無的支那內學院,始有法義之諍。海潮音創刊出版。此期間,多作評論世學的文字,旨皆在於破攝世學而引歸佛法,同時也開了參用演講方式來講經的佛門新例。又鑒於俄國革命成功,共產思想日見流行,故其極力發揚中國禪的風格:「務人工以安色身」「修佛學以嚴法身」,這是針對「僧眾分利」的世詬而發。對佛學的態度,則極端反對以進化論的歷史考證法來研究佛書,比如大乘起信論及楞嚴經,被日本學者考為偽典,這是虛大師最最不忍的事了。而支那內學院即持相反的意見。 三十三歲,鑒於僧寺內腐外摧,而唱「僧自治說」:「須擯絕撓亂之他力——官府之摧殘,地方痞劣之欺;尤應去除本身腐敗之點,力自整頓而振興之!」同時倡導「佛之因行」:「盡吾人的能力,專從事利益人群,便是修習佛的因行。」「以敬信三寶,報酬四恩為本,隨時代方國之不同而有種種差別。」時有「佛法大系」之作,為其大乘三宗論(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識宗、法界圓覺宗)的雛型。那時講說不倦,而謗毀誣控也來了。 三十四歲,出圓覺經隨順釋科目,又作「對辨大乘一乘」,「對辨唯識圓覺宗」,三重法界觀。唱道大乘平等,而宗本天台、禪宗、得學要於楞嚴經、起信論。歐陽竟無主張法相與唯識分宗,太虛大師則主張法相必宗唯識,這又是與內院諍論之點。時有人將虛大師與諦閒長老,分為新舊兩派,而其二人,的確是始終走著相反的路線。那年游廬山,認識梁啟超,並由武漢佛教會請其與梁啟超等作佛學演講。武昌佛學院成立,僧俗兼收,法尊與法舫,就是那時的學僧;課程參取日本佛教大學,管理參取禪林規制,早晚禪誦,唯念彌勒。回向兜率淨土為異。為駁歐陽竟無的「唯識抉擇談」而作「佛法總抉擇談」,為起信論辯護。 三十五歲,作「評大乘起信論考證」,而對梁啟超採用日本考證的論點,加以反對,而說:「日本於今日,所以真正佛學者無一人也!」在那年舊歷新年,由武院學生張宗載、寧達蘊發起的新佛教青年會編行「佛化新青年」出版,這是大師佛教運動中的「急進派」,以「農禪工禪」,「自食其力」,「和尚下山」等為口號。那年夏天去廬山,主持暑期講習會,並於大林寺發起世界佛教聯合會。復對佛學院的僧教育提出計劃:小學、中學、學戒、大學、研究院,共分五級,以二十四年學程,養成行解相應的僧才。又以大師終是以泛承中國本位舊傳諸宗為本,支那內學院則特宗深密瑜伽一系,故其雙方常有法義之諍的文字。 三十六歲,編成「慈宗三要」,於其特弘彌勒淨土,至此乃確然有所樹立,同時又作「志行自述」,確定了「志在整興僧(住持僧)會(正信會),行在瑜伽菩薩戒本。」他是主張僧眾與俗眾分頭並興的。又提出職業與志業之說:「故學佛之道即完成人格之道,第一須盡職業,以報他人資吾身命之恩;第二乃勤志業,以淨自心進吾佛性之德。」而主張人人有事做,人人皆學佛。那年春夏間,虛大師的門下,以狂熱為教的革新精神,引起長老不安,各方震動,並有以印光大師為第一號魔王,諦閒老為第二,范古農為第三,馬一浮為破壞佛法的罪魁的傳單印發。又因其在家弟子王弘願學密,而引起僧俗顯密之諍。武院的學生第一屆畢業,擬改革,而不得大部分院董支持,所以失敗了。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虛大師所倡的世界佛教聯合會於廬山開第一屆會議,並定名第二年在日本舉行者為「東亞佛教大會」。當時在大師之下有佛化報、海潮音、佛化新青年等雜誌。十二月,虛大師發生兩種新覺悟:「中華佛化之特質在乎禪宗。」「中國人心之轉移系乎歐化。」主張以禪、律振興佛教,以佛法播於國際而變易西洋學者的思想。? 三十七歲,春天,武院同學會出版「新僧」,由大醒、迦林、寄塵負責,老僧為之驚恨,虛大師遂作「箴新僧」,以緩和老僧的惡感。是年,虛大師多以儒學為佛化的方便,主以1建佛法以建信基,2用老莊以解世紛,3宗孔孟以全人德,4歸佛法以暢生性。其至晚年發揚中國文化之論點,要亦不出於此。並轉變振興中國大乘佛教以救世界的方針,為先著手於世界運動,格化西方,故令學僧會覺、大醒等學習英文。是年廈門南普陀,請常惺法師創辦閩南佛學院。當時的東密與藏密,亦成為中國佛教的氾濫混亂的局面。故作「今佛教中之男女僧俗顯密問題」,講「論即身成佛」及「中國現時密宗復興之趨勢」,主張納於教理,軌以戒律,嚴其限制。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組代表團出席在日本召開的東亞佛教大會,深得日人的推崇,尊之為「佛教界之盟主」,並有「非常」之感。虛大師至此,並得一理想:「佛教徒當首先進行佛教的國際組織」,而應以僧伽負責,尤其不滿日本式與蒙藏式的「耽妻室、甘肉食而為僧」的佛教生活。 三十八歲,應汪大燮、熊希齡等發起的北京講經會之請,在北平中央公園社稷壇,開講四十二章經。又應京中教育界所組的佛學研究會之請,講「佛法概論」,以「因緣所生法」為五乘共學;「三法印」為三乘共學;「一實相印」為大乘不共學。條理佛法之義理為三階,此為大師晚年的定論。八月二十日赴星洲弘化,十月二十日回國過廈門,與在廈門的名士魯迅、顧頡剛等見面晤談,魯迅對大師的印象是「和易近人,思想通泰」。 三十九歲,元月講「佛之修學法」於尚賢堂,其對佛法的重要意見,悉攝於此。復感所作「僧伽制度論」已失時效,而作「僧制今論」。為了改良經懺而設法苑,希望以此除去迷妄,擴大組織,獲得經濟基礎,用作新僧運動,但是失敗了!又因歐陽竟無主張在家人可為出家人之師,得受出家人的禮拜,故作「與竟無居士論作師」以責之。十月作「真現實論」,大師獨到的思想,多含攝其中,足以貫攝一切佛法;破攝一切世學;他說「佛陀為無主義之現實主義者。而現實主義,雖鏡涵萬流,含容一切,要非佛陀不足以正其名也。以簡別世俗現實主義,故名曰真現實論。」是年十二月,又著「自由史觀」,他說:「吾人正當之所為,唯自用自由源泉之心知活動,自解放重重被囚之桎梏,以增進其自由而完成其自由之本性耳。」這是大師的名作之一。至此,大師的主要思想,已經完成了。可惜的是,他所計劃中的真現實論,共分「宗依」「宗體」「宗用」的三大部,宗依論是完成了,宗用論是編集文化、宗教、哲學等單篇的文集,至於宗體論,他預計有理、行、果、教、教理行果等五大章,但僅寫出初章,他就去世了,真是眾生的福薄! 四十歲,因為在建僧事業上屢受挫折,對於建僧的信心大減,故有「或轉身從事於十善菩薩行」的返俗意念。閩南佛學院由大師命大醒及芝峰去主持學務。大醒編行「現代僧伽」,多涉人之臧否,為老派所痛心。是年內政部長薛篤弼,提議改僧寺為學校,中大教授邰爽秋,擬有廟產興學的具體方案,大師因作「對於邰爽秋廟產興學運動的修正」,然當時佛教尚無政府認可的合法組織,交涉不易,因而提出佛教的革命方案,主張建設佛僧、佛化、佛國的三佛主義。並說:「中國的佛教革命,決不能拋棄有二千年歷史為背景的僧寺」,而要「以人生佛教,建中國僧寺制」。故講「人生的佛學」:「佛法雖普為一切有情類,而以適應現代之文化故,當以「人類」為中心,而施設契時機之佛學。」是年六月應蔣中正先生邀,大師謁於司令部,告以放洋日期。並得蔣中正先生的贊同而成立中國佛學會籌備處於南京萬壽寺,此為國民政府下,中國佛教始有正式組織的雛型,但因教內不合作,老上座、名居士別有用心而致失敗了。八月十一日,赴歐美游化,自上海登船,經香港、西貢、星洲、錫蘭、埃及的開羅,船行凡月餘,始初抵法國的馬賽。發表「西來講佛學之意趣」,他說:「歐洲今富聖人之才而缺聖人之道,吾人今有聖人之道而乏聖人之才。有道乏才,即不足證其道;富才缺道,則不足以盡其才。得聖人之才以授聖人之道,是為吾至歐講佛學之總意趣。」後至英國、德國、美國,經夏威夷而返國,此次歐美之遊,除了講佛學,活動的目的,則在籌創世界佛學院,然其努力至最後,此一計劃終於失敗了。唯在歐美地區的佛學宣化,則深具影響,所遇者均是名流學者,所至者多為文化學府及學術團體。直至第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才回國抵上海。 四十一歲,大師的徒弟大愚,自謂於廬山閉關念佛,見普賢現身,授心中心咒。因此在上海好言宿命,以神奇惑世,哄動全國,大師屢戒,不唯不聽,其徒屬反而誹毀大師,大師的正信弟子王森甫等,也受其惑,但在未幾之間,大愚便鎩羽潛形了。是年大師以政府的管理寺廟條例,不利佛教,而作「佛寺管理條例之建議」。又以建議未被政府採納,而作「評監督寺廟條例」。三寶歌的歌詞,亦為那年所作。 四十二歲,大師以叢林精神盡失,政府又未能扶助佛教,佛教會亦難得改善,乃重新議訂建僧計劃為「建設現代中國僧制大綱」,主以「三寶之信產生僧格」以「六度之學養成僧格」。建僧四萬人,分學僧、職僧、德僧三段。此於僧伽制度論的觀點頗有修正。以往所倡「人工之新僧化」,及「僧制今論」的服勞大眾,至此已棄而不論了。是年康藏留學團的大剛,不滿大師弘化的苦心,以及建設世界佛學院的本意。而兩次電報,望大師先往西藏修學正法,再事弘通。 四十三歲,四月間出席全國佛教徒會議,被選為執行委員,會議改選,大師派獲勝,會址設於首都,中佛會之成立,至此始獲中央黨部的認可。但以圓瑛法師不合作而辭去常委,諸山承認的經常費亦不繳,使會務無法進行,大師鑒事難行,亦於六月聲明辭職,這是大師組織教會的又一次失敗。是年又因有大師門下揭諦老之隱,而招諦老徒屬對大師的誹毀。大師又提出他對僧教育的理想:「一支為汰除的僧教育,使之退為沙彌或優蒲,以習農工而自食其力;一支為考取的僧教育,使之入律儀院二年,教理院七年,參學處三年的學僧。由選拔為職僧,推定為德僧者以主持佛教。」但此始終未能實現其少分。 四十四歲,在世界佛學院的計劃之下,去年北平柏林學院因經費支絀而停辦,是又在重慶北碚縉雲山,創辦漢藏教理院,正式開學。十月,應奉化蔣先生延請,住持雪竇寺。又於閩南佛學院開示學僧:「現代學僧所要學的,不是學個講經的儀式,必須要能實行佛法,建立佛教,昌明佛法,而養成能夠勤苦勞動的體格,和清苦淡泊的生活。」十月,應廈門大學教授所組文哲學會之約,講「法相唯識學概論」。 四十五歲,因有熊十力的「新唯識論」,而與熊十力及支那內學院有法義之辯。 四十六歲,因戴季陶等發起請班禪重開「時輪金剛法會」(去年開於北平),大師就法華經義,作「斗諍堅固中略論金剛法會」,以釋教內外人士對於藏密流行而憂神鬼迷信之禍國的疑諍。並且親自向班禪喇嘛執弟子禮而受金剛阿闍梨大灌頂法。是年隨卻非出家者巨贊與熊東明,歸從支那內學院學。曾編海潮音的弟子張化聲,轉佛而入道教。九月,大師講「唯生哲學」於東方文化研究院(由讀陳立夫的唯生論而來),其結論謂:「唯物論是淺的唯生論,唯識論是深的唯生論。苟善知唯生之義,則一切學術皆可作唯生論之參考,以成其唯生哲學。」 四十七歲,有人勸太虛大師於雪竇寺開壇傳戒,便作「論傳戒」,他說:「今戒種斷而僧命亡矣。續命之方,其惟有集有志住持三寶之曾受?芻戒者二三十人,清淨和合,閱十年持淨?芻戒律,然後再開壇為人受?芻戒。」向被認為是新派領袖的太虛大師,對於戒律亦持如此審慎和沉重的態度者,恐非一般人所知之事。那年,他已感到體力漸衰,而將留了二十年的鬍子剃掉,勉自振作為青年。又因中日佛學會內有巨贊及熊東明,作文指大師及其門下為勾結日本人,為害國族的誣控。故作「告日本佛教大眾」以表明心行。是年五月於南京中國佛學會,講優婆塞戒經,發題日,他便論及「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有謂:「非研究佛書之學者」、「不為專承一宗之徒裔」、「無求即時成佛之貪心」、「為學菩薩發心而修行者——本人系以凡夫之人,得聞佛法,信受奉行者。」這是虛大師很有價值的自白。是年十月有一錫蘭比丘公然聲言「中國無僧伽」,大師乃特晤約,與之論辯,開頭就說:「中國原有僧律之成立,時至今日,遵行律之僧伽較少耳。然說「中國無僧伽」,將中國僧伽全體否認,殊非合理。」十二月十六日,應虛雲老之邀,訪韶關南華寺,瞻禮六祖遺身。並為大眾開示。 四十八歲,五月,大師聞知生平最誠摯的益友昱山病逝。五月三十一日,作「論僧尼應參加國民大會代表選舉」,但為歐陽竟無致書陳立夫反對之,以為「僧徒居必蘭若,行必頭陀」,「參預世事,違反佛制。」七月,日本大學請虛大師東渡講學,大師拒絕了。時訓總監部,今各地僧侶,編入壯丁隊受軍訓,大師電函二中全會等,請一律改僧尼為救護隊訓練,以符佛教宗旨。是年中國佛教會,圓瑛法師派,運用各方關係,故得勝利,虛大師對中佛會的改組運動,因之受挫!是年適逢蔣先生五十之慶,大師於雪山設藥師法會為之祝壽,又值西安事變,大師通電全國佛教徒,聯合各別祈禱,祝蔣先生安全。 四十九歲,芝峰編「人海燈」,與會覺、亦幻假名作「新佛教人物的檢討」,於大師略有微訾。大師因而對其員生講「新與融貫」,明示其所謂之新,與芝峰、亦幻等的新,有所異趣,主張「佛教中心的新」及「中國佛教(華文)為本位的新」。而不是「奔趨時代文化潮流或浪漫文藝的新」;不是「憑個己研究的一點心得,批評中國從來未有如法如律的佛教,而要據佛法的律制以重新設立的新」。可見虛大師的新思想,一開始就被他的門人誤會。是年八月,即進四川,直到抗戰勝利始離開。那年,他已很明顯地感到「身心」的「早衰」了,故作「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以示徒眾,希望後起,應知他的弱點及弱點的由來而自矯自勉。他說他本身的弱點:「大抵因為我理論有餘而實行不足,啟導雖巧而統率無能。」他說他失敗的由來是:「出於個人的性情氣質固多,而由境遇使然亦非少。例如第一期以偶然而燃起了佛教革命情緒;第二期以偶然而開了講學辦學的風氣;第三期以偶然而組織主導過佛教會。大抵皆出於偶然幸致,未經過熟謀深慮,勞力苦行,所以往往出於隨緣應付的態度,不能堅牢強毅,抱持堅固。」那年又為日軍侵略,憂心國是,而電「告全日本佛教徒眾」,又電「告全國佛徒」,呼籲抵制侵略。 五十歲,三月,在漢藏教理院講「中國的僧教育應怎樣」,他說:「養成『住持中國佛教僧寶的僧教育』,不過是我的一種計劃,機緣上,事實上,我不能去做施設此種僧教育的主持人或領導人。而且,我是個沒有受過僧教育的人,一切的一切,都是你們——教的人及學的人,不能倣傚的,倣傚我的人,決定要畫虎不成反類犬,這是我的警告」。「余以身力衰朽,已不能實際上去做準備功夫,或領導模範的人。」這些話,都是他的真心話,也是感歎語,他已努力了近三十年,能夠響應而繼起者,簡直沒有人,所以頗感失望,但他自此以後,仍為佛教做了很多事。是年與章嘉大師及虛雲長老商決,在重慶成立「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 五十一歲,元月十四日,常惺卒於上海,年來常惺法師任中國佛教會秘書,與圓瑛法師合作,而虛大師始終愛其才,故作詩追念。是年三月,著手寫自傳。四月三日,復亦幻書,論革新僧制與復興佛教。他對亦幻說:「你向來頗好文藝,而於佛法勝義未加研究深入,對一般哲學與各種社會學亦鮮探涉,偶及馬(克思)說,故亦同一般淺薄少年的驟然傾向。其實,近人的文化社會學,亦遠勝馬氏之說,況於佛法之所明耶!為佛教徒而不信佛法為根本的、至極的、唯一的思想標準,則所謂破見,較之毀戒尤甚!直可捨佛而去,何用更自居佛徒而以改佛制為言耶?!」「余民四年,揆度我國將成一歐美式的民主國,故作「整理僧伽制度論」,為適應之建設,然以國內軍閥割據,政變迭生,及歐洲戰後俄國革命成,形勢異前;迨民十六,遂適應改為「僧制今論」。民二十後,外感世界經濟大恐慌,內覺中國佛教會,無由有全國之健全組織,另為「建僧大綱」之擬議,今更縮為先建一「菩薩學處」。……然其屢變,皆與整個中國相呼應而起,且皆從佛教根本信念流出。從這封信可以看出虛大師的苦心與偉大處,但也看出他的門下如亦幻之流的思想趨向與淺薄程度了。是年九月,為了爭取國際同情中國的抗日戰爭,虛大師組織「佛教訪問團」,訪問西南各國,十一月十四日啟程,抵緬京(瓦城),受二千餘緬僧及萬餘中、緬、印人士之歡迎;至仰光,乘花車游行,參加遊行群眾三萬餘人。 五十二歲,訪問團於元月九日自緬赴印度,十一日抵加爾各答,歡迎者中印各界領袖二百餘人;十七日出席國際大學歡迎會,八十高齡的泰戈爾親臨主席;三十一日,尼赫魯訪問虛大師,並談論中日戰爭及中印文化交流等問題;二月三日,赴拘屍那的途中,沿途民眾歡迎,大師記之以詩:「甘地尼赫魯太虛,聲聲萬歲兆民呼。波羅奈到拘屍那,一路歡騰德不孤。」印度人民將虛大師與甘地尼赫魯並呼萬歲,可見歡迎情緒之一斑了;二月十二日,應甘地電邀而於紡紗聲中虛大師與之交談,太虛大師作詩贊甘地為古墨子,喻泰戈爾為活莊周;二十四日抵錫蘭科倫坡,晚開歡迎會,到會者萬餘人;二十七日晚,又有萬人歡迎大會。於離開錫蘭,即抵星加坡。四月二十八日抵西貢,五月二日抵河內,四日抵昆明。結束了五個月來的訪問工作,完成了偉大而具卓效的外交任務。至此,虛大師的建僧態度又一變,主張僧青年深入嚴林而施格化,較之別創僧團為便;並以為政教合一,不如分離,而保持僧伽的超然地位。同時又提出整個僧團的主張:「今後應停止剃度女尼二十年;並嚴限非高中畢業男子正解正信佛法者,不得剃度為僧,以清其源。……對於原有僧尼,嚴密淘汰,不妨以大部分寺庵,改為佛教之救濟所與感化所而收容之,以潔其流。」復提出「菩薩學處」的計劃,以期改建佛教徒眾,此為其晚年的建僧定論。但卻由「僧伽制度論」的建僧八十萬,「僧制今論」建僧二十萬,「建僧大綱」四萬而二萬,至此「菩薩學處」則縮小而得「一道場」以創行了!即使一道場的菩薩學處也未建立成功! 五十三歲,計劃組織太虛大師學生會,但卻組而未成。是年二月,曾編海潮音的唐大圓卒於湖南。為了抗日,虛大師作「出錢勞軍與佈施」之廣播;漢藏教理院的學僧,亦參加重慶青年夏令營。 五十四歲,由於「頃為藉征警糧,或藉辦鄉鎮中心小學等,拘逐僧人,占提寺產」,而作「呈行政院維護寺僧」。是年有馮玉祥、郭沫若等訪問虛大師。 五十四歲,民國三十二年元月十四日,與陳文淵、馮玉祥(基督教)、於斌(天主教)、白崇禧(回教)發起中國宗教徒聯誼會。二月十七日歐陽竟無卒,大師𥐰有「我尤孤掌增哀」之句。是年於漢院講「中國佛教」,對中國獨創之佛學,作一縱貫之敘述,講歷一年。那年內政部頒布「寺廟與辦公益慈善事業實施辦法」,致各地佛教陷於紛亂,大師乃召集中國佛學會理監事聯席會議,發電呼籲反對,內政部不允取消,大師乃致書蔣先生,作悲憤之陳辭,而得停止實行。 五十六歲,號召各省佛教代表,來集陪都,除呼籲取銷「寺廟與辦公益慈善事業實施辦法」,且呼籲組成中國佛教會,但因內政部意在提寺產辦學,大師與戴季陶屈文六等商洽向內政社會兩部疏通成立佛教整理委員會,由內政部指派整理委員九人,提寺產辦學之案無形打銷。是年三月十五日,大師訪教育部長陳立夫,得允免漢院員生緩役事,又訪軍政部長,以全國僧侶免役從事救護工作為請。六月十二日,行政院指令軍政部,准免漢僧服常備兵役。八月九日虛大師初次中風。初冬,蔣先生游縉雲山與大師晤談。 五十七歲,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四日,太虛大師以德國投降,乃作「告日本四千萬佛教徒」,勸其慨然無條件投降。八月十日,日本真的無條件投降了。九月十四日,虛大師離開住了八年的縉雲山。 五十八歲,民國三十五年元月一日,虛大師受政府勝利勳章。當時,虛大師深覺僧伽應問政不干治,可參加各級民意代表之選舉,辦理組黨,亦無不可,但虛大師本人不願參加黨的實際工作而作罷。是年四月抵南京,五月抵上海,頗受歡迎。七月於上海創刊覺群週報,發表了「問政不干治」之主張。 五十九歲,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日,於廷慶寺開講「菩薩學處」,凡三日,此為虛大師的最後說法。二月十七日,虛大師晚年最器重的青年學僧福善,卒於上海玉佛寺,因福善的風度,頗似虛大師的青年時代,致大師慟惜非常。三月十二日為玉佛寺退居震華封龕說法且竟,忽腦溢血而昏厥,至十七日下午一時一刻,於玉佛寺直指軒安祥捨報。一代佛教的偉人,至此溘然長逝了!失敗的成功者一部長達五百四十四頁的太虛大師年譜,我以不足一萬字的篇幅來濃縮它,實在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但我為了簡略地將太虛大師的一生介紹出來,所以如此做了;為了明白太虛大師的成敗得失,所以如此做了。 我們看了上面的介紹,可以說,虛大師的一生,是完滿成功的;但也可以說,他是完全失敗的。他在理想的追求與創造上,總是站在時代的尖端,也總是站穩著佛教本位的立場,他所行的,沒有不是他所想的,所以他對他個人的理想建設的開創,以及他對他的宗教人格的建樹,都是完整而飽滿的;但在對外的事業上,卻是一個最最不幸的失敗者或犧牲者。因他站在時代的尖端來提拔這一時代中的國家、佛教、群眾與青年,但是大家的智能太低,思想太舊,眼光太淺,所以接不上他。他要整頓佛教,組織教會,大家都怕他、避他,乃至恨他;他要興辦教育,作育僧材,在他教育下的弟子們,卻又不接受他、不瞭解他、不滿意他,乃至叛離他與反對他。 因此,太虛大師的教育是失敗的,而且是失敗在他的門徒手裡;太虛大師的搶救佛教僧侶與寺廟的努力,也是失敗的,而且是失敗在他所要搶救的僧侶及寺廟之中! 從舊派的角度看太虛大師是新僧新派的革新運動者,所以他在廣大保守的佛教群眾之中,雖受重視,但卻並不受到敬仰,所以他在這方面的號召力,不及諦閒及圓瑛,在宗教情緒的潛勢力,又不及印光、弘一、虛雲三大師的影響力之深而且長。 從新派激進分子的立場看太虛大師,乃是一個半新半舊甚至近乎保守的人物,因為太虛大師的新作風,新思想,是推陳出新,以佛教信仰為本位的新,而不是除舊更新的新,更不是一味狂熱破壞的新。所以他的那班淺薄的門生,要對他不滿和失望,乃至脫離他,背信他。 在研究的態度方面,太虛大師反對以歷史進化論來考證佛典,乃是為了維護他自己的信仰,也是為了維護傳誦了千百年的佛典如楞嚴與起信等的尊嚴。但他處此一切求證據的時代潮流之中,很難力排眾議而得不敗了,所以近世在教外的思想界中,談起佛學,又多喜引支那內學院的論例為論證。故在一這方面,太虛大師又是失敗的。 最可嗟歎的,太虛大師雖未能將他理想中的僧教育制度實現,但他擁有武昌佛學院、韶南佛學院及漢藏教理院等三所培植僧青年的佛教學府,但在他所培植出來的僧青年中,竟無一人能夠接受他的思想,並且如大醒、芝峰、張宗載等門生,還常以激進而粗率的文字,攻擊舊派,而為太虛大師招致對方徒屬的無理誹諦,這簡直是為他拆台而非擁護!最後,芝峰還了俗,張宗載走入了歧途,不再信佛。為了僧裝改革的問題,慈航也憤激揚言要脫離新僧。太虛大師從事僧伽制度及僧伽教育近四十年,最後竟然如此,實是很難令人置信的事! 這有一個最大的原因,那就是如他自己所說,他對他的事業「往往出於隨緣應付的態度輕易散漫,不能堅牢強毅,抱持固守」,「大抵皆出於偶然幸致,未經過熟謀深慮。」但這也不能怪他,因為他的悲心太重,而這個時代的病痛太多了,也太深了!他見到一種病痛,便不由自己地要去醫治一種病痛,見到了無數的病痛,便不由自己地要去醫治無數的病痛,希望能夠醫好這個時代中的所有病痛。無奈,他的精力有限而時代的病痛多而且重!在他的一生之中,自二十二歲以後,他的一切活動,無非是在醫治這一時代的病痛。但是,病家要跟醫生合作,病痛才能痊癒,如果雖病而不接受醫生的勸告及治療,再好的醫師,也是沒有辦法。有人說,太虛大師是近代佛教的病理學家而非生理學家,說他只能為佛教看病,卻不能為佛教治病。實際上的太虛大師,既是優秀的病理學家,也是傑出的生理學家,試看他的一生,他不曾專度「象牙之塔」型的隱士生活,他的數度閱藏與閉關,最久也僅廿八個月。住得最長久的地方是縉雲山的漢藏教理院,但他未嘗只找問題而不實踐其問題的解決途徑。奔走呼籲,足跡幾遍全世界,為的只是救人、救世、救佛教,育僧、護僧與建僧。他的理想,雖未能夠實現其少分,近代的佛教,卻因他的出世而帶來了許多的安全與新生的希望。他在佛教會的組織上雖然失敗了,佛教會的創立,卻是由他而來;他在呼籲建僧的努力上雖然失敗了,中國寺廟之未被政府全部提去,僧尼之未被勒令滅絕,卻又多分得力於他的維護;他在僧教育的建樹上雖然失敗了,近代僧教育之尚能維持著私塾式的一線命脈,卻又要溯源於他對僧教育的倡導。今日的知識僧人,多半也與他的僧教育的努力有關,他所提倡的「慈氏宗」及「人間佛教」的理想,雖未實現,今日之有「人生」或「人間佛教」的觀念者,受他的影響很大。 所以,我們的時代以及我們這一時代中的人們,既辜負了佛教,也辜負了太虛大師。太虛大師對於我們的時代以及我們這一時代中的人們,確是功德無量,恩惠無量的。 一言以蔽之:我們進步得太慢了,我們這一時代中的人心太自私了,這一時代中的青年太膚淺了,所以辜負了太虛大師的努力。正像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運動,是一種救國救民的運動,但他努力了四十年,還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直到他逝世後的今日又是四十年,國民革命尚在繼續前進中。太虛大師的境遇,實與中山先生是一樣的!直到現在為止,佛教徒中又有幾人是真能為整個佛教的前途著想的呢?他們在受到外力侵擾時,會想到希望佛教會來保護的需要,卻何嘗想到如何整頓佛教與振興佛教?如何來為佛教作育人才,如何來促進組織的健全與堅強的問題了?即使各級佛教會的領袖們,也多得過且過,未作長遠的計劃! 寫到此處,不勝感慨系之!我雖不是太虛思想的發揚者和實踐者,卻是太虛精神的崇仰者。我想:如果太虛大師的悲心稍微輕些,他在事業上或學術上的成就,當會更加卓越些,正因他的一生,皆在「隨緣應付」中匆忙度過,所以未能專志於某一志業的貫徹始終。他對他學生的思想教育的失敗,也正因他未能悉心負起教育的實際責任,他雖主持了三個頗負盛名的佛學院,但他並未能以全部精神放在教育的工作上。他的接引的善巧是成功的,所以因他而信佛學佛的人很多,往往於一次法會之中,有成百成千的人皈依三寶,他對知識分子的接引,似乎還特具方便;但他在化與導的努力上是不足的,是不能維繫長久的,所以也是失敗的。在他行化的一生之中,雖有許多的弟子,卻未能有一位是生死不渝而能繼承其思想與事業之衣缽的大弟子;這在負有同樣盛名的古德之中,實是一位寂寞的大師。也許是我們的時代,只需要如此的太虛大師,來維護這個青黃不接的佛教局面,所以太虛大師也就順應此一時代的需要而「隨緣應付」了吧! 但是,太虛大師是一位卓越成熟而成功的宗教家,也是一位光榮偉大而崇高的失敗者;他的精神是成功的,他的事業是失敗的——這是我對太虛大師的結論。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七日脫稿於朝元寺 (刊於海潮音四十六卷三及五月號)?
|
||||||||||||||||||||||||||||||||||||||||||
| 版權沒有,在註明出處的情況下,歡迎轉載。另請善心佛友在論壇、facebook或其他地方轉貼本站連結,功德無量。No CopyrightDvNews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