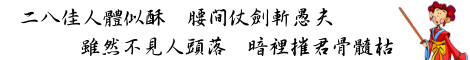蘇軾(一○三七∼一一○一年),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省眉山縣)人。他是北宋著名文學家,詩文革新集大成的人物。又活躍於宋神宗、哲宗朝政壇,在當時影嚮很大。神宗時,王安石主政變法,他一再上疏,反對新法,因此屢遭斥黜,以至被罪謫黃州。神宗死,新法廢,他入朝後又與執政者不合,再次被斥出朝。到哲宗親政,新黨得勢,則又被遠貶惠州、昌化,直到死前才得北返。他生活在矛盾衝突十分複雜的時代環境中,滿肚皮不合時宜,左右支絀,動輒得咎。他一生思想很複雜。他本是歐陽修的後學,然而思想趨向與歐陽修的堅持儒家「道統」截然不同。但他立身行事,正當敢言,剛腸疾惡,自稱「賦性剛拙,議論不隨」。《宋吏》本傳上說他「忠規讜論,挺挺大節」,這都表現他堅持儒家大義,力行兼濟的品格。然而他又好縱橫之說,對佛教則崇信彌篤。他自青年時期習佛,晚年習染漸深,自稱「居士」。這種複雜的思想矛盾統一到他身上,是文學史、思想史上值得重視的現象。
蘇軾的家學淵源,個人教養與他後來習佛關係很大。他的故鄉四川地區自唐代以來佛教就甚為發達。我國第一部官版大藏經,以後中國官方和民間以及高麗、日本刻藏所依據的所謂「蜀版」,就是在宋初刊刻於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的。蘇軾的父親蘇洵,結交蜀地出身的名僧雲門宗圓通居訥和寶月大師惟簡,僧傳把他列為居訥法嗣。其母程式也篤信佛教,父母去世時,蘇軾曾將其生平愛玩遺物施之佛寺。蘇軾在「十八阿羅漢頌敘」中,曾記述家中有十八羅漢像,供茶則化為白乳等等。這都可見其家庭中的宗教氣氛。蘇軾與弟弟蘇轍極其友愛,這是歷史上的佳話,而蘇轍也是熱心的佛教徒。他在與蘇軾唱酬詩中寫道:「老去在家同出家,楞枷四卷即生涯」。「目斷家山空記路,手披禪冊漸忘情」。蘇軾的繼室王氏閏之亦學佛,她於熙寧七年(一○七四年)從蘇軾,到元祐八年(一○九三年)病逝。蘇軾在其生日曾取「金光明經」故事,買魚放生為壽,並作《蝶戀花詞》,中有「放盡窮鱗看圉圉,天公為下曼陀雨」之句。她死時有遺言,令其子繪阿彌陀佛像供奉叢林,蘇軾請著名畫家李龍眠畫釋迦佛祖及十大弟子像供奉京師,並親為作《阿彌陀佛贊》,說「此心平處是西方」。蘇軾妾朝雲也學佛,早年拜於泗上比丘義沖門下。後與蘇軾一起到惠州,經常念佛。至紹聖三年(一○九六年)死前彌留時仍誦《金剛經•六如偈》,蘇為制銘中有云:「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悼朝雲詩》說:
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夜燈勤禮塔中仙。
家族中的這些情形,與蘇軾都有相互影嚮。
蘇軾直接與佛教發生關係,是在二十幾歲初入仕任鳳翔簽判的時候。初習佛於同事王大年。他在《王大年哀辭》中說:
嘉祐末,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軍••••予始未知佛法,君為言大略,皆推見至隱以自証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書,蓋自君發之。他的作品最初寫到佛教題材的,是嘉祐六年(一○六一年)所寫的《鳳翔八觀》。其第四首,(口+永)唐著名雕塑家在鳳翔天柱寺所塑維摩詰像,詩云:
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龜。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雲隨。世人豈不碩且好,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卻千熊羆。••見之使人每自失,誰能與結無言師。
這裡表現了他對著名的維摩居士的嚮往。但他理解的維摩詰是一位不懼死亡、身如浮雲的「至人」。此後在其一生詩文中,常常寫到維摩詰,並常常以之自比,本詩是個開端。
蘇軾步入政壇,正是王安石變法從醞釀到開始發動的時期。這位脫穎而出的青年幹才與改革派政見不合,不久即被斥出朝。先是熙寧四年(一○七一年)通判杭州。從而使他陷入現實矛盾之中,早就習得的佛教教義最易於在這種苦悶中發生作用。而杭州自吳越以來就是佛教興盛之地,西湖周圍風景優美地區佛寺之眾冠於全國,高僧雲集。僧人中有不少是很有文化教養的人,與蘇軾自然願意相互結交。蘇轍《偶遊大愚見余杭明雅照師舊識子瞻能言西湖舊遊將行賦詩送之》一詩回憶說:「昔年蘇夫子,杖履無不之。三百六十寺,處處題清詩。麋鹿盡相識,況乃比丘師。辯、淨二老人,精明吐琉璃。笑言每忘去,蒲褐相依隨。」
蘇軾在《祭龍井辯才文》中說: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辯、瑧,禪有璉、嵩。這裡的「辯」,指海月法師慧辯和辯才法師元淨。二人同為明智大師弟子。慧辯(一○一四∼一○七三年)修天台宗,為杭州都僧正,講教二十五年,學徒及千人。蘇軾曾為作《海月辯公真贊》和《吊天竺海月辯師三首》。辯才(一○一一∼一○九一年),住天竺觀音道場,蘇軾對他與慧辯一樣「敬之如師友」。蘇軾有《贈上天竺辯才師》詩寫道:
南北一山門,上下兩天竺。中有老法師,瘦長如鸛鵠。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見之自清涼,洗盡煩惱毒。坐令一都會,勇丈禮白足•••。
可見蘇轉對他的尊敬。蘇轍《龍井辯才法師塔碑》中記載,蘇軾「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請師為落髮,摩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如他兒」。「瑧」指梵臻,天台知禮高足,住上天竺,後遷金山寺,又為南屏山興教寺住持。《佛祖統紀》卷十二曾記載「東坡初來杭,與師最厚」。「璉」指懷璉(一○○九∼一○九○年),師事圓通居訥,與蘇軾為世交。這個人在皇室和親貴間廣泛活動,後來到金山和明州阿育山隱居。蘇軾有《與大覺禪師璉公書》,是為布施蘇洵所藏禪月大師羅漢圖而作;又有《宸奎閣碑》,是為廣利寺中懷璉收藏皇帝所賜頌寺詩十七首的宸奎閣所寫的碑文。「嵩」指契嵩(一○○七∼一○七二年),是前面提及的《輔教篇》作者,為雲門緣密圓明三傳弟子。他死於蘇軾到杭州的半年之後,蘇軾在《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中曾提起他,說「予在錢塘,親見二人」。以上是五個人。此外與蘇軾往還密切的還有孤山惠勤、惠思。蘇軾在熙寧四年到官三日就去拜訪過。又有詩僧清順、可久,前者住錢塘門外祥符寺,後者住寶岩院。還有宗本禪師,住南屏山下淨慈寺。所以蘇軾說:「吳越名僧與余善者十九。」他又寫到自己與惠辯的交往:「予方年壯氣盛,不安厥官,每往見師,清坐相對,時聞一言,則百憂冰解,形神俱泰。」可知他結交僧侶的情景與心情。
對蘇軾的佛教信仰產生重大影嚮的另一件事是他被貶黃州(今湖北省黃岡縣)。他本來對變法不滿,一些附和革新派的人利用他的詩文進行羅織,搞成一個文字獄即後來所謂「烏台詩案」,使他飽受折磨和屈辱。如果說在此以前他對佛教還多是感性的接觸,與杭州名僧結交也是六朝以來文人、高僧之間相交往的高風逸趣,那麼在經受現實苦難之後,他就進一步追尋佛理,企圖從中得到安慰與解脫。蘇轍在給他寫的墓誌中說:
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
蘇軾有《和子由四首•送春》詩,中有句云:「憑君借取《法界觀》,一洗人間萬事非(來書云近看此書,余未嘗見也--原注)。《法界觀》即宗密所作《注華嚴法界觀門》,這是發揮華嚴法界緣起理論的重要著作。他初到黃州時,住在一個佛寺裡,隨僧蔬食。現實的一切使他灰心杜口。他在《與程彝仲推官書》中寫到這個時期情形:「但多難畏人,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黃州時期,蘇軾又結交了了元佛印禪師和詩僧寥參。了元曾遍參禪宗名僧如居訥等,住江州承天寺、淮上斗方寺、廬山開先寺等寺院,以及金山、焦山,名動朝野。寥參大概在蘇軾早年任徐州通判時即已相識。這兩個人後來一直與蘇軾保持著十分親密的關係。
神宗死,王安石變法失敗,保守派主政,這就是所謂「元祐更化」時期。蘇軾回朝,但遇事不隨,又與當政者多齟齬。因此又再次通判杭州。後來他說到「余去杭十六年復來,留二年而去,平日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他這裡所謂「似樂天」,當然包含著兩人同喜結交方外、熱衷參禪的內容。早在黃州時,他就自號東坡居士。「東坡」這個名字即取自白詩,「東坡居士」則是仿白居易稱香山居士而製作的。此後他常常以樂天自比。
紹聖年間,新黨再度執政,蘇軾也再遭流貶,遠到惠州和海南。在赴惠途中,過金陵崇因禪院見長老宗襲,院內有新造觀音菩薩像,蘇前去禮拜並發心願:「吾如北歸,必將再過此地,當為大士作頌。」後果然於北返時為作《觀世音菩薩頌》。又南行經曹溪南華寺,即原來的寶林寺,本是六祖惠能傳法之地,作《南華寺》詩。紹聖四年再貶海南,告命到惠州,惠守說其妻曾夢見普光王菩薩僧伽將為其送行,蘇軾則以為「前世有緣」。元符三年(一一○○年)北歸,再到南華寺,未至前友人蘇賢在南華寺相待,蘇先寄一詩,有句云:
水香知是曹溪口,眼淨同看古佛衣,不向南華結香火,此生何處是真依。
這裡「眼淨」用《維摩經》「遠離塵垢,得法眼淨」典。又有《追和沈遼頃贈南華詩》:
善哉彼上人,了知明鏡台。歡然不我厭,肯致遠公材。莞爾無心云,胡為出岫來。一堂安寂滅,卒歲扃蒼苔。
對比起來,他前期寫到佛教的詩,往往流露不堪世事壓迫以求解脫之感;而到後期,則能以更透脫的禪理來認識世界,看待人生,作颯然超離之想。
蘇軾習佛,與許多文人一樣,內容是很龐雜的。他不是一個對理論思辨有興趣的人,更不是專精義學的理論家。從其詩文經常引為典據的佛經看,他最熟悉的是《維摩》、《圓覺》、《楞枷》諸經以及禪師語錄等。他說「久參白足知禪味」,對禪特別表現出興趣。另外如前所述,他曾研習華嚴著作。華嚴宗提倡法界緣起,以為事理無礙,大小等殊,理有包容,相即相入,萬事萬物都是一真法界的體現,因此互相包含,互相反映,無窮無盡。他的詩中也寫到這種觀念,例如:
孤雲抱商丘,芳草連杏山。
俯仰盡法界,逍遙寄人寰。
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
若人了此言,地獄自破碎。
但淨土觀念在他身上沒有白居易那麼濃重。在他對佛教的理解中,理智的追求佔有更大的比重。明顯的表現是他有些時候也曾批評佛教中宣揚的頹廢超世和因果報應觀點。例如他在居喪期間,應惟簡之請,寫《中和勝相院記》,其中說: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吾嘗究其語矣,大抵務為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
因此他認為某些佛教宣傳是「為愚夫未達者」所設的「荒唐之說」。這指的主要是淨土信仰。他在《大悲閣記》中又說:
至於為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為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通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為。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而嘻而已,是為大以欺佛者也。
這裡批評的則是禪宗無言無相之說。他的這種說法與柳宗元對禪宗的批評相似,也是以理性批駁神秘主義。
另一方面他也主張釋與儒合。例如在《宸奎閣碑》中他寫到懷璉:
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與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遊。
又《祭龍井辯才文》說:
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鍾,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
他稱贊懷璉能調和儒與佛、老;對於辯才,則指出其在佛教宗派間取兼容態度,實際是闡揚他整個思想的弘通。根據事理圓融的觀點,不但佛教各宗派,就是儒、佛、道各家都有其價值,共同匯合到一個真理的汪洋大海中。而在儒釋二者之間,他以為相反而相為用,不謀而同。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即出世間,等有無二。所以他對二者都不偏廢。他在《答畢仲舉書》中說到自己學佛的立場:
佛書舊亦嘗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仆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為至矣,而鄙仆所言為淺陋。仆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仆之所學,豬肉也。豬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仆之食豬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與仆輩俯仰也?••
這就表示他的學佛,不喜歡那些玄虛之談,而希望在身心上真能得益。他所說的「淺陋」,正是與現實人生有關聯處。他顯然不相信佛教真能讓人出世作佛,而希望它對俯仰人世的平凡人有益。這種對待佛教的態度,有相當的理性色彩,也是他能對各家思想學說取開闊眼界的原因。
蘇軾對佛教的這種獨特理解,表現在詩作中,也形成了特殊內容。
蘇軾之好佛,首先是要求靜心。現實世界帶給他無數苦悶與煩惱。在佛教中,他學到擺脫這些煩惱的超然態度,可以在一時間跳出矛盾糾纏之外,從而達到心泰神寧。但在許多情況下,他又並沒有完全超世入佛,而往往只是在解脫「煩惱障」之後對人世冷眼觀察,結果對一切苦難都無所掛礙,無所顧念。他在《海月辯公真贊》中說:
予通守錢塘時,海月大師惠辯者實在此住,神宇澄穆,不見慍喜而緇素悅服。予固喜從之遊。
他每見惠辯,清坐相對,即達到形神俱泰的境界。他在《黃州安國寺記》中又說:
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蓋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污自落,表裡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但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
這裡寫出了他入佛寺習佛時的心情。他在那裡,與其說是求福祐,不如說是求清靜。在佛寺的清幽環境中焚香默坐,悟得物我雙亡、身心皆空的道理,心境上也就安寧了。這是由於內心反省所得到的安慰。
他有一首《書焦山綸長老壁》詩,寫得很有風趣,也透露了對人生的理解。這種理解可說深得禪機。詩云:
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我來輒問法,法師了無語。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故。君看頭與足,本自安冠屨。譬如長鬣人,不以長為苦。一旦或人問:每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著無處。展轉遂達晨,意欲盡鑷去。此言雖淺鄙,故自得深趣。持此問法師,法師一笑許。
這是「借禪以為詼」的作品。他用一個長鬣人的比喻,生動風趣地表現一種對人生的透脫理解,也說明了禪宗求淨心的道理。長鬣人對他的鬍子本來是不以為礙的,但一旦有人提醒,對它有了自覺,反倒不知所措,連覺都睡不好了。這裡既說明了不可膠著於外物得失,同時也表現一種為人處世之道。他在詩文中經常寫到那種「安心」的境界,如:
因病得閑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道人不惜階前水,借與匏樽自在嚐。安心好住王文度,此理何須更問人。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卻當年覺痛人。未知仰山禪,已就季主卜。安心會自得,助長毋相督。
還有些詩不用「安心」這個詞,但意思是相同的。如:
欲問雲公覓心地,要知何處是無還。
這裡用《楞嚴經》:「我今示汝無所還地。」又如:
散我不平氣,洗我不平心。
我心空無物,斯文定何間。
君看古井水,萬象自往還。
他在文章中也多有表現這種心境處,如《大悲閣記》:
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
這裡寫的是外物不擾於心,以靜心觀照萬物的接物之道。同時在觀照中體察物理,這又是用華嚴法界事理圓融思想來闡述淨心。他在惠州建閣曰「思無邪」,並作《思無邪齋銘》,有云:
東坡居士問法於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未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中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於是得道,乃銘其齋曰思無邪••
這裡所謂「有思而無所思」,深得佛家「中道」三昧。有思指無邪之思,就是後面所謂「正念」,而無所思指不為外界所干擾。他要這樣做到外輕內順,即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以此了解生理,則內心自然平靜了。而把佛法的「正道」與孔子的「思無邪」相統一,正是他統合儒釋的表現。蘇軾《阿彌陀佛頌》說:「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無盡處,則我與佛同。」這樣,在他看來,人生罪福苦樂,都決定於一念之間,應物處事只決定於主觀的認識與態度。這種看法是純屬唯心的,是一種自我心理安慰,但又表現為一種不以物喜、不為己擾的超脫情懷。
蘇軾還經常講「人生如夢」。《赤壁懷古》中的感慨是人盡皆知、十分感人的。「如夢」是大乘十喻之一,是佛家人生觀的表現。佛家講「如夢」,是因為我、法兩空,比中國固有的老、莊思想深刻得多。他的詩裡經常抒寫這樣的感慨:
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回頭自笑風波地,閉眼聊觀夢幻身。人間何者非夢幻,南來萬里真良圖。願君勿笑反自觀,夢幻去來殊來已。舊事真成一夢過,高談為洗五年忙。此身自幻孰非夢,故園山水聊心存。
這樣,蘇軾感覺到人生是虛幻的,世事也是虛幻的,「一彈指間去來今」,這顯然受到大乘空觀的影嚮。這些詩的基本情調是消極的,但其中也包含著對於人生的理智的反省。既然人間一切都是夢幻,那麼人生的痛苦也不過是幻影,人世的功業名利也沒有什麼價值。這就導向了對當時社會所承認的一切有價值的東西的否定,和對於苦難現實淡然處之的態度。他的《百步洪二首》中以流水比喻人生,意思也相似:
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念逾新羅。紛紛爭奪醉夢裡,豈信荊棘埋銅駝。覺來俯仰失千劫,回視此水殊委蛇。君看岸邊蒼石上,古來篙眼如蜂窠。但應此心無所住,造物雖馳如余何。
「一念逾新羅」,《傳燈錄》典:有僧問金鱗寶資大師,如何是金剛一只箭?師云:過新羅國去。說的是迷念之速如射箭一樣。蘇軾看到了歷史紛爭,人間劫奪,瞬息萬變,一切如過眼煙雲,因而他表示要斷除迷念,心無所住,也就是不膠著迷戀於現實事物。他認為不論世事如何變化,只要自己在認識上都能適應,那麼就會安時處順,無所執著了。
蘇軾從早年起即學《華嚴》。華嚴法界萬法平等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也有明顯表現。他在《怪石供》中說到以怪石為供,有云:
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根據大乘空觀,諸法性空,寶玉與瓦礫、石頭都是「平等」的。因為這些事物,都是一真法界的體現。如果用這種看法對待人生,就會泯是非、齊榮辱,通達無礙,不忮不躁。他在詩裡也經常寫到這種心情:
至人無心何厚薄,我自懷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都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我今身世兩悠悠,去無所逐來無戀。太山秋毫兩無窮,巨細本出相形中。大千起滅一塵裡,未覺杭、穎誰雌雄。更慶勞生能幾日,莫將憂思擾衰年。片雲會得無心否,南北東西只一天。
萬法平等,所以萬物各得其所,禍福苦樂只是相形而現,是人們的感覺而已。在一切都在生滅流轉的世界中,什麼計較都是不必要的。紹聖二年貶惠州時,他給程之才寫信發表感想:
某睹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話妙理達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
在這樣的心情之下,流貶的痛苦不以為意,也就寵辱不驚、處險若夷了。
蘇軾對佛教態度的一個特點,就是利用佛教的觀念,對人生進行理智的思索。在深刻的反省中,求得心理上的平定。有時候,他覺得自己並沒有完全領會佛說。他在《答參寥書》中自我檢討說:「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為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為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他給友人寫信中,還說到自己雖然慕佛道,誦《楞枷》,但實無所見。這些當然有謙虛的意味,但也說明他對佛道並非那樣執著、迷信。他的兒子蘇過曾為其亡母王氏寫《金光明經》,問他此經是真實語還是寓言,他為之重述了張安道的話:「佛乘無大小,言亦非虛實,顧我所見如何耳。萬法一致也。我若有見,寓言即是實語;若無所見,實寓皆非。」他認為佛語的真實與否以至佛的有無,都在心的一念。這種非有非無的通達觀念,與虔誠的迷信很不相同。正如前已指出,他十分讚賞維摩詰。他曾用維摩詰來稱頌別人,如對前輩張安道:
樂全居士全於天,維摩丈室空翛然。平生痛飲今不飲,無琴不獨琴無弦•••。
對朋友文與可:
慇懃稽首維摩詰,敢問如何是法門。彈指未終千偈了,向人還道本無言。
他更經常以維摩詰自比。維摩詰周流世界、遊戲人間而又能以無限睿智來對待世事的態度,是蘇軾非常欣賞的。他是白居易以後在文學中宣傳居士思想最有力的另一個人。
蘇軾生活在中國封建文化已經爛熟的時期。他本人是具有高度文化素養的封建士大夫的典型。他多才多藝,文、詩、詞無一體不佳,書、畫等無一藝不精。在思想上則縱橫儒、佛、道,廣取博收,旁推交通。佛教思想給了他不少消極影嚮,但卻始終沒有佔據他思想的全部。就其對佛教的理解說,一方面他對其頹廢面有所警惕,如在《答畢仲舉書》中說:「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無害。」另一方面由於他能利用佛教觀念對人生進行反省,培養起一種超然、灑脫的人生態度。這種觀念與儒家用世思想相互為用,則處危難間不懼不餒,而一有機遇又能堅持理想,奮鬥不已。蘇轍說他謫居海南時「日啖薯芋而華堂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即使到了晚年,詩文中亦不見衰憊之氣。這也表現出一種氣節。所以佛學修養也有使他得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