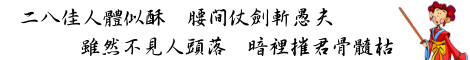本報記者 漏丹 北京報道 2004-12-6
11月5日。深夜。34歲的王芳終於用跳樓自殺的方式擺脫了艾滋病。
凌晨四點,孟林接到了王芳的死訊,當時他正在上海一幢大樓的十層上,他說自己也有跳下去的衝動。
「她一直以為自己屬於那1%永遠都不會發病的人群。感染艾滋病以後,她已經什麼事兒都沒有地活了十多年。」11月10日,同是艾滋病感染者的孟林陷在沙發裡,不停地抽著煙。40多歲的孟林很瘦,瘦到不能坐硬板凳,稍坐一會兒就得來回挪騰。孟林是在今年年初認識王芳的,兩天前,在王芳的遺體火化儀式上,他們見了最後一面。王芳只是孟林送走的人之一,自1980年代末感染艾滋病毒後,和他同時感染、同時發病的人已全部離開人世。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在11月23日公佈的最新報告,今年全球有4000萬人攜帶艾滋病病毒,亞洲已經成為艾滋病傳播最為迅速的地區之一。根據中國的官方統計,2004年中國的艾滋病感染者已超過100萬。
「艾滋病的發展有五個期。第一期是吸毒人群,第二期是同性戀人群,第三期是性工作者,第四期是婦女,第五期是兒童。現在我們國家已經進入第四期。」北京佑安醫院的護士隋雪英說。50歲的隋雪英已在佑安醫院工作了31年,從1996年開始照顧艾滋病感染者。今年,中國性病艾滋病協會在佑安醫院正式成立了艾滋病關懷與治療委員會,隋雪英是成員之一。
隋雪英說,艾滋病向婦女和兒童蔓延,前景會很不樂觀,意味著艾滋病從高危人群蔓延到普通人群。當「2010年,中國感染艾滋病的人數將達到1000萬」的警鐘敲響之時,社會接受了艾滋病,但不是艾滋病患者。
「原罪」
1991年,正在蘇州上大學的藝術系學生王芳愛上了一個剛從國外回來的男人。同居之後,男友告訴王芳,他身體裡有艾滋病毒。因為沒有使用安全套,王芳就這麼被感染了,從此她有了不能對別人說的「原罪」。
那個時候,年輕的王芳不知道安全的性行為必須正確使用安全套。「90年代初,什麼宣傳都沒有。安全套是計劃生育用的東西,跟預防艾滋病完全沒有關係。」孟林笑得很辛酸。
1997年,王芳的男友發病了,已經來到北京工作的王芳飛回蘇州見了他最後一面。臨死前男友表達了自己內心的愧疚,但為時已晚。
平靜地度過十多年後,去年7月,王芳因為感染弓形蟲突然發病。
她不知道該上哪個醫院去看病。雖然在北京工作多年,她沒有一個朋友,不認識一個艾滋病方面的醫生,也不認識一個同病相憐的感染者。她只能每天躺在家裡,情況一天比一天糟糕。發病之前,她雖然一直與蘇州某防疫站站長保持聯繫,但他沒有告訴她,艾滋病毒感染者需要定期做CT4細胞檢測和病毒載量檢測,如果健康狀況下降到一定程度,就需要開始服用抗病毒藥品。他只是不停地賣給王芳中草藥。
得知消息的家人在網上查到佑安醫院後,王芳才第一次進醫院治療。命暫時保住了,但是身體崩潰了。
「王芳挺有才的,琴棋書畫都行,長得特別漂亮,像跳芭蕾的那種女孩。」多次去過王芳家裡的隋雪英回憶道,「但是發病後,她半身不遂,手老跟挎著籃子似的,走路瘸了。有一段時間出不了門,生活都不能自理。」
「其實王芳的情況,哪怕早兩個月發現,開始吃藥,還來得及。」孟林遺憾地說。現在國內抗病毒藥品價格最低的只需要每個月3000多元,已經不是孟林當初發病時的情況了。但是,如果社會不多一點寬容,沒有更多關於艾滋病的科學宣傳,僅僅有藥物是遠遠不夠的。
與王芳相比,孟林要幸運得多,他雖然病得早,但是遇上了好人。
1996年初,孟林出現了典型的艾滋病發病症狀:高燒不退,腹瀉嚴重,肺部感染,全身淋巴結腫大,並且出現了非常嚴重的皮膚潰瘍。
大年三十,孟林撥通了他一直鎖在抽屜裡的佑安醫院艾滋病咨詢處的電話。初二早上九點鐘,當時佑安醫院的艾滋病咨詢醫生徐蓮芝遵照約好的時間迎著風在醫院門口足足等了四十分鐘,孟林終於出現了——他一直在對面的公車站觀望著徐大夫。
「當時徐阿姨微笑著迎了上來,拉著我的手從後門走進診室。因為過年,診室裡面沒有人,她用自己的一雙手給我做檢測。」孟林邊說邊做手勢,「她的表情很嚴峻,感覺出我的情況已經很嚴重了。」
「孟林在大年三十晚上第一次打電話時,徐主任當時已經回家和家人團圓去了。值班醫生讓孟林過十分鐘再打,並把情況告訴了徐主任。徐主任馬上趕了過來。」瞭解當時情況的隋雪英說。但是當晚,孟林沒再打電話。大年初一,徐蓮芝又趕到醫院,終於在晚上接到了孟林的來電。
1990年,佑安醫院收治了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但是直到1996年初醫院還沒有專門收留艾滋病人的病房。
那一年的3月中旬,徐大夫終於向醫院爭取到一排總共五六間的小平房作為艾滋病人的病房。「說是病房,其實是一間二三十平米的小庫房,離太平間只有一牆之隔。我進去後心都涼了。」孟林說。病房陸陸續續進了五個人,治療條件非常簡陋。
「任何人在生命面前不該冷漠。」聽說醫院要成立艾滋病病房,隋雪英是第一個報名加入的護士。「搞醫的人很容易就弄清楚傳播途徑不外乎那三種,關鍵是對病人的態度。我覺得從尊嚴、人格上來說,人都是一樣的。即便感染者當初做錯了什麼,他們的行為已經首先給自己懲罰了。其他人就應該在他們最低潮的時候拉上一把。」
到1996年年底時,五個病友只剩下孟林還活著,其餘四人不是病死了,就是自殺了。孟林的情況也不樂觀,喝一口水都會全吐出來。
「九幾年的時候國家還沒引進什麼艾滋病藥。雞尾酒療法有是有,但是價格很貴,藥也不多。」隋雪英說。
徐大夫把這種吃一年要花20多萬的藥的消息告訴了孟林。當時這種藥只有一個渠道能進到國內,由一位醫生以私人身份從國外直接購買。
孟林賣了房子,得到了第一年的藥費。從1997年1月20日起,他開始服用從美國進口的抗病毒藥品。到今天,他花在艾滋病藥品上的錢至少已有200多萬。
這些錢大都是孟林從1996年開始做生意賺的錢。為了賺錢,他開過歌廳,做過各種亂七八糟的生意,他毫不諱言地說自己做過很多虧心事。「這些年掙扎著過來了。如果只是實幹傻干,那我也早就死了。」他承認自己是社會渣滓堆裡出來的人。
孟林採用的雞尾酒療法藥物價格在1998年到2002年間下降到每年十幾萬,到2002年底,下降到每年84000元,到2003年4月下降到每個月不到4000元。
生活
今年年初,孟林在佑安醫院認識了王芳。不到一周,王芳就決心要嫁給孟林。雞尾酒療法藥物的副作用讓她變得很抑鬱,每天都在設想怎麼自殺,她渴望身邊能有一個人陪伴。
但是孟林開始逃避王芳,雖然他每天都會和王芳通幾個小時的電話。
孟林認為艾滋病人好比是一座危房,自給自足還有危險,更不能再承擔任何附加的風險了。兩個感染者走到一起,從正面來看,彼此能夠給予心理支撐,但孟林想得更多的,還是一連串的責任和問題。
「結婚是一種責任。感染者夫婦如果不要孩子還好,萬一有了孩子,孩子很可能成為孤兒,如果孩子也感染了,那就更悲慘了。夫妻間還會有交叉感染(艾滋病病毒有不同的類型)問題,以及一系列的生活問題,這些能否承受得起呢?」孟林說。他承認自己自私,是「真小人」,但總比偽君子強。
按照孟林的說法,伴隨了他十多年的病毒,已經把他變得「沒稜沒角,沒血沒肉,沒心沒肺」。
孟林得知自己患有艾滋病的當天,就打電話把事情告訴了兄嫂。哥哥非常婉轉地要求孟林離開這個家。於是在那個很寒冷的夜晚,孟林背著行囊「出國」了——這是對老母親的說法。
「剛剛被判死刑,就被遺棄了。」孟林這樣總結最辛酸的往事。之後他常常在公園裡偷看母親晨練;他很少給母親打電話,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緒。
孟林心裡恨著自己的哥哥和嫂子。1997年初,他病得不行的時候,醫生問要不要告訴家裡人,他一口拒絕了。「我當時這麼說,死了怎麼處理都行,燒了順著馬桶一衝,或者找個樹坑一埋,都行。活著他們不管,死了他們還會管嗎?」
「在醫院住到死,就別回家了。九幾年的時候,很多家庭都是這樣對待感染者的。」隋雪英說,「現在情況好多了,我們醫院這邊,還沒有哪個家庭拒絕感染者回家的,但是家人埋怨的情緒還是有的。」
孟林說,感染者要學會欺騙自己,每一分鐘都要欺騙自己。
每天午夜,出門遛彎兒;每天看電視,直到每個台都道再見;每天讓自己想很多別人的事情;每天逃避感染者圈子裡的人;每天在網上閒聊;空閒的時候出門旅遊。這些是孟林欺騙自己的幾種方法。
自從1996年確診感染艾滋病後,孟林重新開發了一個生活圈子。對於從前的朋友、同學、同事、親友,他就像人間蒸發了一樣。
死亡
在孟林感染艾滋病的早期,每當有感染者離開的時候,他都會去送送這些人,向他們的遺體送上一束鮮花,不管是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
孟林說從這些感染者身上,他也看到了自己。他用這種方法調節自己,使自己有勇氣面對最後的結局。通過這種方式,孟林克服了自己對死亡的恐懼。
但是王芳的死還是讓他受到了巨大的刺激。
王芳跳樓的時候穿了衣服,但屍檢完成以後,她身上的衣服沒有了。赤裸的屍體被裹上了兩層裹屍袋,為此工作人員還向家屬收取了額外的消毒費。「打開的時候,真是……人哪……滿身滿臉的血污!」見到王芳屍體的時候,孟林失控了。
王芳的家人帶著她的衣服趕到火化的地方。隋雪英當時也在場:「我想我過去能幫她洗洗擦擦,讓她穿上衣服乾乾淨淨的走。」
但是工作人員拒絕了這個請求。40分鐘以後,一盒骨灰送到了家人的手上。
「活著,尊嚴沒有得到足夠的尊重;死的時候,一點尊嚴都沒有。古時候就算窮人死了,也會用一張草蓆裹一下,不能光著走啊……」孟林幾乎開始控訴了。隋雪英在採訪時也感歎:「王芳死的時候這麼沒有尊嚴。」
死亡時的尊嚴,一向是孟林看重的,也是他擔心的。
孟林還記得1998年10月20日,那天有一位感染者在佑安醫院去世。他曾經是一個一表人才的小伙子,但在住院一年多的時間裡沒有一個親人看望過他。
在這個小伙子病危到大小便失禁時,醫生和護士不停地給他擦拭,孟林和另一位病友在一旁幫忙。病人嚥氣以後,也是他們把病人的身體擦乾淨,換上了乾淨的衣服。一個多小時以後,家人終於來了,卻連病房都沒有進,屍體被直接推進了太平間。
那天正好輪到隋雪英值班:「我給他家人打了兩次電話。家人說,他好的時候隋老師你那麼細心照顧他,現在就剩下這最後一哆嗦了,我們相信你一定會照顧好他的,等他嚥氣以後,你再通知我們吧。」
當這個病人的屍體還在病房的時候,孟林、那位病友和隋雪英三個人擊掌為誓,立下了一個生死之約。孟林流著眼淚對隋雪英說:「姐,我哪天不行了,那會兒不管你在哪兒你在幹什麼,都要回來給我穿好衣服。」
採訪結束時,孟林說了這樣一句話:「你明白嗎?不是離開,是有尊嚴的離開。」
(在此文發表時,孟林正在雲南參加國際艾滋病聯盟組織的感染者藥物醫從性會議。孟林並不是他的真名,每個艾滋病感染者在以感染者身份出面時都會有一個固定的代號,這個代號也用於住院或接受治療。感染者之間,包括各個艾滋病組織、國際基金會甚至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都像醫院一樣,只知道各個感染者的代號。文中提到的王芳也是一樣的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