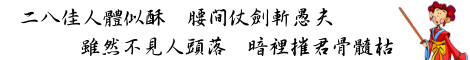往事百語1 -- 心甘情願 星雲法師著
難遭難遇
| [日期:2008-05-30] |
作者:星雲法師著 |
閱讀: 次
|
我的一生中,有許多信念與習慣,其中,「難遭難遇」這四個字令我畢生受用無窮!
我出生在歷史上著名的魚米之鄉──江蘇揚州,我覺得這是一件「難遭難遇」的美事。家父忠厚老成,家母精明能幹,童年庭訓,愛的攝受與力的折服,兼而有之,我感到真是「難遭難遇」。在很自然的因緣下,禮志開上人披剃,他有著恢宏的氣度,不希望我終生隨侍在旁,因而及早將我付諸十方大眾,進入叢林苦修,我能投皈在這麼偉大的師父門下,實在是「難遭難遇」。
我出家的地方,是有「六朝聖地,千佛名藍」之稱的棲霞山。在古寺深山裡十年,我看到春暖花開的寺周桃杏,也看到深秋漫山的楓葉,我接受善知識炎熱嚴威的考驗,也嘗到寒冬冰雪般的嚴峻教化,成就了我的法身慧命,我衷心感到「難遭難遇」。及至行腳臺灣,先是落腳在佛寺中,搬柴、運水、拉車、採購……無所不做。後來,又替人看守林產,日夜巡山,這一切「難遭難遇」的經驗,無不是在磨鍊我的心志,長養我日後淬勵奮發的道念。
來臺後,由於生性內向,故先投入佛教文化圈中,編輯佛教刊物,但以食宿無著,而改從事佛教教育工作。未久,卻遭佛學院因故停辦,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得鼓起勇氣,走入社會弘法。就在這種機緣下,我開始與大眾廣泛接觸,養成我「以眾為我」的習性,可謂「難遭難遇」。
二十五歲至三十歲時,多少國家邀我講經弘法,但我因不懂英文,只得婉拒好意;多少寺院請我主持法會,我也因不擅梵唄唱誦,而辭卻盛情。現在想想:正因為如此,我才得以安心辦道,專意以弘法利生為家業己志,這何嘗不是一種「難遭難遇」的因緣呢!當時臺灣寺廟囿於思想保守,不易接引青年學佛,欲培養佛教人才,唯有自設道場一途。佛光山,就是在這種理想下開闢而成。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有的困難阻撓、貧乏空無,無一不是「難遭難遇」的逆增上緣。
一九八五年,我自佛光山退位後,承各方信徒愛護,未曾將我遺忘,這裡邀我講經,那裡請我弘法,在盛情難卻之下,日子未見清閒,反益形忙碌。馬不停蹄的雲遊行腳,足跡遍布海內外,使我結緣更廣。雖然舟車勞頓,總有一股「難遭難遇」的法喜,鼓舞著我精進不懈。「國際佛光會」這個世界性的佛教組織終於在一九九二年五月中旬誕生,各地會員也正急遽增加之中,佛教發展至此,可謂永劫剎那,「難遭難遇」。
別人給予我的慈悲關懷、喜捨協助,即使是點滴恩惠,在我心目中,永遠都是「難遭難遇」的善緣。例如:四十年前在宜蘭弘法時,物資缺乏,一文不名,每天只能就著一架破舊的縫紉機上撰寫文稿。數個月後,信徒將附近監獄中即將丟棄的書桌揀來給我使用。供養雖非珍珠瑪瑙,出自一片誠心,卻是「難遭難遇」。
年輕時,經年累月,三餐不飽,一位老太太阿綢姑常常送來一碗麵、兩片麵包,給我止饑。清夜自捫:我何功何德?彼此又是萍水相逢,承她厚愛,把我當作師父或是兒子看待,此種恩情,「難遭難遇」。王鄭法蓮老太太與我素無深交,但憑一股信佛虔心,拿了我所撰寫的《無聲息的歌唱》和《玉琳國師》,沿門兜售,竟然各賣了兩千本。我所有初期弘法和教育事業,一盒粉筆、一個幻燈機,她都贊助,在人情紙薄的社會裡,尤其感到「難遭難遇」。現在我將高齡九十多歲的王老太太接來佛光精舍居住,頤養天年,也算聊表寸心。
二、三十年來,不少青年學子隨我出家為僧,本著「有教無類」的精神,我對他們犧牲奉獻,現在有八百僧伽之多,更有許多護法居士,奉行佛光山「人間佛教」的宗旨,尤以支援建寺,幫助印經,發心服務,出錢出力,這一切的一切,令我不時有著「難遭難遇」的感受。
春風秋雨固然可以潤澤群生,秋霜冬雪也可以成熟萬物。青少年時,師長們無情的打罵,無理的要求,孕育我服從、堅忍的性格,使我安然度過人生中的每一個驚濤駭浪,這種「難遭難遇」的教育方式,實在功不可沒。
初出道說法,往往為一句講辭、一段例證而斟酌半天,案牘勞神,及至今日,在各地奔波,或廣開大座,或隨緣法施,信口道來,只覺得俯拾即是佛法。大眾慈悲,肯聽我演講,促使我深入經藏,慧解薰修,每思及此,唯有一句「難遭難遇」,足以略表心中無限感激。
有人欺騙我時,自忖我是出家人,就必須寬大為懷;有人毀謗我時,自思我是出家人,就不會尋仇報復;有人加害我時,自許我是出家人,就需以慈心相向。長年經歷困頓蹇厄的環境,並沒有將我打倒,唯願天下蒼生皆得福祿壽喜;經常遇到無理取鬧的眾生,也沒有令我氣餒,唯有祝禱法界有情智慧如海,明理通達。所有的冤親債主、榮辱毀譽,透過「難遭難遇」的信念,化為忍耐、寬容,便能逆來順受,甘之如飴。
生命中一切好壞榮衰,都因為我有了這個凡事作「難遭難遇」想的性格,而使我的人生充滿了喜樂與幸福!
(佛光廿六年-一九九二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