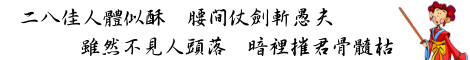往事百語2 -- 老二哲學 星雲法師著
先作牛馬,再作龍象
| [日期:2008-05-30] |
作者:星雲法師著 |
閱讀: 次
|
家師志開上人是佛教的實業家,他除了教書課徒之外,還興辦宗仰中學、棲霞律學院,同時也非常重視佛教的經濟實業發展,並效法百丈禪師的自食其力農工的修行生活,曾經整治山林、創辦農場、燒窯生產、設置染織場。家師在成立這些事業的時候,為了要向政府辦理登記,必需湊夠人數,所以把當時十五、六歲的我也登記了進去。他恐怕我不懂得此中的意義,而有所異議或感到疑惑,還特地叮嚀我說:「你將來要想作『佛門龍象』,現在就得先作『眾生牛馬』。」這句話我一直奉行不逾,回想佛門的高僧大德不都是「先作牛馬,再作龍象」嗎?
像佛世時,舍利弗尊者除講經說法之外,還負責精舍工程的監督,所以能威服群倫,助佛宣化;陀驃比丘在悟道之後,自願充任知客,每天起早待晚,提燈幫忙前來參學的比丘安單,後來感得手指發光的瑞相。唐朝的志超法師勤勞眾務,每有苦役,必事身先,晝夜克勤,攝引後學,因而得到時人擁戴,數百僧侶翕從學習,法席隆盛。道亮法師六載舂米,曾無廢惰,後來講律,聲被東夏。宋朝道法禪師白天將乞食所餘,咸施蟲鳥,夜晚則脫衣露坐,以飼蚊蚋,一日入定,見彌勒菩薩放光照耀,因而更加精勤。雪竇禪師甚至不願出示大學士曾鞏的推薦信函,寧可陸沉靈隱寺中,操持作務達三年之久,後為龍天推出,駐錫雪竇山資聖寺時,從此海眾雲集,宗風大揚。溈山靈祐禪師及趙州禪師更是令人敬佩,一個發願來世作老牯牛服務大眾,一個希望往生後到地獄度眾。而在社會上,以「牛馬」精神服務大眾,而終能以「龍象」之姿成就事業者,更是不勝枚舉,如王永慶以賣米白手起家,高清愿從基層學徒做起,林肯童年時曾做過木工、雜工學徒,富蘭克林少年時曾擔任蠟燭工、印刷工。所謂「英雄不怕出身低」,真正的「龍象」,不怕「牛馬」般苦役的考驗;真正以眾生「牛馬」自居者,也不畏「龍象」的踐踏磨鍊。
記憶中,我的一生似乎都和勞動、苦行結下不解之緣,好在我從小出生在農家,練就了結實的體力,舉凡車水、除草、牧牛、收割等庄稼人必備的本領,我都必須學習,甚至農忙之餘,我還得陪著外婆開闢菜園,種植果蔬,以維持家計。記得那時,外婆就經常對我說:「有志沒志,就看燒火掃地。」不時地告誡我:「從小一看,到老一半。」要求我做事時必須認真努力。我將這些話謹記在心,一直把「工作最神聖,服務最偉大」視為一生的格言。
出家之後,我到棲霞律學院就讀,也是從為人添飯、管理茶水、看守山林、搬運木柴等基本作務開始學起。到了暑假,我們每天得早出晚歸到山上採無花果,以增加常住收入;寒假雖然為期稍短,但仍然忙得不亦樂乎,尤其農曆春節的大掃除,單單擦拭全寺的玻璃就要花掉一個月的時間。每逢乾旱時期,我還發心到江邊挑水,一次來回要三個鐘點左右。後來,到焦山佛學院繼續學業,除了上課之外,還兼作管理油燈、燒煮飯菜等事務。總之,勞動的工作從來未停息過一天。由於白天忙於勞動服務,晚上沒有照明設備,因此我就以拜佛、打坐來消磨時間,真正讀書的時間並不多,但奇怪得很,我對佛法的體會卻能夠與日俱增。現在想來,才明白那種如「牛」似「馬」般忙碌的作務生活,使我活學活用,讓我「讀」遍長老大德行事的風采,「讀」盡寺院運作的方式,「讀」通生活中修持的要訣。佛學院結業之後,我回到祖庭大覺寺,因為那裡擁有數百畝的土地農莊,我在教書之餘,又恢復兒時農家的生活,與稻麻菽麥、鋤頭耙鏟為伍,從大自然中擷取源源不斷的資糧。
我初到台灣時,雖然在寺院裡從事的都是一些像拉車、打水、收租、採購等粗重的事情,但是因為一直習於勞力的工作,所以不但不覺得厭煩疲累,反而深深感念能有繼續鍛鍊身心的機會。尤其最令我高興的是,儘管過去在大陸不曾有過建築道場的經驗,然而由於具備長久的農工雜務基礎,一旦有了機緣,就能夠得心應手,勝任愉快。像最初在宜蘭建設念佛會講堂時,因為我每天觀察施工情形,對於砂石計算,門窗裝置,磚瓦搬運,刨木雕刻,澆灌水泥等了然於心,所以後來再開工興建慈愛幼稚園的時候,在土木工程方面也就十分駕輕就熟了。
我從宜蘭來到高雄之後,面對一個與宜蘭鄉鎮截然不同的城市,我必須更加兢兢業業,努力以赴。所以從高雄佛教堂到壽山寺的建築,對於一磚一瓦,一沙一石,我都不敢掉以輕心,總是觀察再觀察,研究再研究,所以在如何節省、如何趕工等細節方面,又多加一層認識,由此奠定我對土木工程的興趣。
那時,我每天除了忙著寫稿、編書、教課及一些行政事情之外,一有餘暇,便關心各地建築的外觀式樣及內部設計,並且不斷地思考:「如果是我,我會如何如何去做……。」因為有了這些概念,所以後來建設佛光山時,雖然請不起專業的工程師、建築師,只是和木工出身的蕭頂順先生在泥地上邊談話,邊計劃,既沒有辦公室,也沒有籌建處,連一張辦公桌都沒有,三十多年來,佛光山一棟棟的建築就在路邊談話商量中一一地完成了。
記得剛闢建佛光山時,經濟十分拮据,每逢假日,我還得親自下廚,為來山的遊客服務,希望多得一些油香,來補助建築經費。為了節省工資,我經常將很多工作從蕭先生的手中再包回來自己做,舉凡搬運砂石、攪拌水泥等需要用力的粗活,都由我和早期的徒眾,如心平、心定、依嚴、依恆等人扛起重任,像淨土洞窟兩邊的圍牆、靈山勝境的廣場、大雄寶殿前面的成佛大道、大悲殿前面的丹墀,還有龍亭、放生池等多處地方,都是在我們師徒同心協力之下完成的作品,外觀雖不精美,但很堅固實用。像「牛馬」一樣的勞動生活不但凝聚了師徒之間的道情法愛,也錘鍊著弟子們的道心悟性。
最不可思議的是,蕭頂順先生和我合作至今,三十年來,所有建設佛光山的水泥工、木工、電工、油漆工仍然還是原班人馬,未曾換人,他也因為承辦佛光山的多項重大工程,而成為工程界的「龍象」,許多建築公司高薪挖角聘請他,但他還是覺得在佛光山做事,可以賺到更多的歡喜及功德,所以一一婉拒。
天生具有服務性格的我,註定我終此一生要如「牛馬」般奉獻人群。記得初到台灣時,我雖上無片瓦覆身,下無立錐之地,但只要看到貧苦的人,我就會不顧一切,盡一己之力給予幫助。一九五二年,花蓮大地震,我連一張公車票都買不起,卻本著「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願心,各地行化,勸募救濟震區的災民;韓戰期間,我四處募集醫藥,設法送往韓國前線救傷;越戰之後,我發起支援購買難民船,搶救越南難民;多少次颱風過境,我和黎元譽先生搶先到災區運送食物;後來世界各國的水澇、旱荒、震災、風難,我除了召集各地信徒捐助外,自己也是罄其所有,解囊紓困,明知車水杯薪,如鸚鵡救火,但只想要盡一點微薄的心意。
由於從童年時代,我就曾經為病患療傷餵食;弱冠之齡,也曾經為亡者更衣安葬,對於生、老、病、死,有著特別深刻的感觸。所以一俟佛光山開山之後,我便陸續興設佛光診所、雲水醫院、佛光精舍、萬壽公墓。佛光山開山時,我將在工程土堆中挖掘出來的骨灰罐暫厝於工地草寮中,與之同寢共眠,直到萬壽堂成立之後,將它們安奉其中,才放下心中的掛念;鄉民將路邊拾來的小孩送到佛光山,常住為他們添購新衣,送他們上學。後來,送來的小孩越來越多,大家同心協力,興建育幼院,好讓他們享有家庭的溫暖。儘管誠心奉獻,如「馬」負重,如「牛」犁田,但也只是點點滴滴,猶如微塵爪泥,無法拯救苦難重重的世界。所以,後來弘揚佛法,淨化人心,成為我一直戮力以赴的目標。
四十多年前的台灣,民風保守,佛教不振,現成的佈教場所難得一見,即使有,也不見得肯出借作為弘法之用,我以露天廣場作為道場,從搬桌椅、拉電線、安裝電燈、放幻燈片中,領略到場地佈置的要點;在徒步弘法、單車佈教的途中,眼望山河,腳踩大地,引發不少說法的靈感;從接觸各式各樣的信徒、各行各業的民眾當中,感悟到各個階層的人所面臨的苦楚;在身經各類人為阻難、各種天災變化中屢仆屢起,深深體會到佛法無限的妙用。五十年來,這許多的體驗躍然於心,後來,觸目遇緣無非妙諦,信手拈來皆是法語,我將之書成條目,從鄉村僻野講到國家會堂,從軍營兵團講到監所牢獄,從企業工廠講到學校會館,從家庭客廳講到機關團體,從寺院道場講到街頭巷尾,從國內山河講到國外海港,從電台電視講到電腦網路,這一生中,不止講了千餘會以上。有人說:「人永遠處於兩難的狀態,因為活著為自己很自私,活著為別人又很辛苦。」而我卻有幸接受佛法的洗禮,自許為「眾生牛馬」,在為芸芸眾生奔波忙碌的同時,還能享有一份自利利他的法樂。
多年來,為了對佛教文化盡棉薄之心力,我好像「牛馬」馳騁於道,一意想著如何前進,幾乎到達忘我的境界。記得拙作《釋迦牟尼佛傳》出版時,因為寺內沒有多餘的桌子,我就用板車將全部的書載到郵局的前面,一口氣包裝了兩千多本寄給讀者,當包完最後一本的時候,已是汗流浹背,濕透衣衫,郵局員工也一直催促離開,因為他們要下班了,但那種歡喜直到現在仍回味無窮。發行一份雜誌,從開始到出版,我一週多次來回印刷廠,經常日食不到兩餐,有時饑腸轆轆,也覺得興趣盎然;為了一本新書的印行,我搭乘數小時的火車到印刷廠去看校樣。當時只有一個心願:「我要為眾生做些事情!我要讓佛法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所以即使一包包的書籍,一堆堆的刊物,無處收藏,我還是歡天喜地的從事佛教文化工作。有時大風大雨來了,為了怕書籍文件給水淹沒了,還得東搬西搬,但我依然樂此不疲。一九六三年,台灣北部淹水,在三重埔的一部藏經被水飄走,當時我正在國外訪問,回來聽說之後,心中一片茫然,只想為這一部大藏經舉行追悼會。
六○年代,我編印過《覺世旬刊》、《人生雜誌》、《今日佛教》,從寫稿、編輯、校對、發行,都是我一人包辦,尤其《覺世旬刊》,每十天一次的發行,就像五趣輪迴一樣,無或暫息,光是寫稿、改稿的辛苦,看稿、催稿的繁瑣,不曾經歷者很難了解其中的味道。
儘管多少個晨昏在文字堆裡度過,多少個深夜在絞盡腦汁中煎熬,既沒有拿過一文稿費,也沒有得過一句鼓勵,但是我心甘情願,在所不惜,尤其看到許多人因此而走入佛門,更是高興不已。後來得慈惠、慈怡、依晟相助,又經過了數十年,目前已經發行到一千四百多期,不但在佛光山與信眾之間負起溝通的功用,而且被許多人視為初入佛門的指引要津。由於《覺世旬刊》的順利發行,又帶動了《普門月刊》的出版,一批批的有志青年投入其中,接受挑戰。多年來,儘管法務倥傯,我卻未曾放棄「文化牛馬」的職志,不時推陳出新。像近兩年來,三百萬字的《佛教叢書》和三十萬字的《佛光教科書》陸續推出,無不是多年來如「牛馬」般服務大眾的切身體會。
二、三十年前,創辦佛教教育事業,高雄師資不多,南部許多老師都是特地從台北延請到佛光山來授課,常常抵達的時候已是深更半夜,但無論多麼晚,我都會佇立在山門口,恭候他們駕到,甚至為他們煮宵夜點心,看著他們吃完就寢,我才安心返回寮房。學院草創初期,沒有經費聘請行政人員,我不但一人身兼數職,還得到殯儀館、太平間通宵誦經來彌補學生食宿開支。後來,慈惠、慈嘉、慈怡、慈容、慈莊陸續赴日深造,我一個人從工友打雜、編印講義到教務行政、輔導訓育,忙得不可開交。一些沒有恆心的學生中途退學,我的心中不知生起了多少的歎息,多少的無奈,但三十多年來,我仍像「牛馬」一樣,無怨無悔地耕耘著這片菩提園地,只為了作育僧才,讓佛法能遠播四海,光照普世。
我這一生,對於某些信徒,或有慚愧照顧不周之處,但我對於大眾的福利,自問一向都是克盡心力,不辭辛勞。就以農曆過年而言,早年我不是在朝山會館幫忙典座,就是到果樂齋炒麵、炒飯,後來有好幾年的春節期間,我都是在指揮交通中度過。記憶中最深刻的,要算是五年前的春節期間,台北道場為募集佛光大學籌建基金而舉辦書畫義賣,我在義賣會的前夕才從泰國弘法歸來,雖不曾學過裝潢美工,但因嫌其會場佈置簡陋,即刻召集徒眾們通宵達旦重新擺設,直到第二天開幕時,雙眼都未曾闔過,沒想到來賓們讚語連連,聽在耳中,真是比什麼獎賞都來得更好。後來,我們以此經驗在各地開設美術館,獲得許多好評,可見無論什麼事都要從「牛馬」做起,才能穩紮根基,立於不敗之地。
除夕夜是大家圍爐團圓的日子,我也經常都是在開示完畢之後,立即趕到山上各個區域視察,從懸吊花燈到工地灑掃,從通宵擺設陳列館的寶藏到熬夜佈置展覽館的物品,我都曾參與其中。六年前,佛光山增購山下土地作為停車場,由於人手有限,負責畫停車線的員工直到晚間圍爐時還未完成工作,我自告奮勇前往幫忙,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四點多才完工,一共畫好大客車停車位八十輛,小客車停車位四百輛,大年初一我守候山頭,看到車輛整齊有序地排在停車場,給予信徒們多少方便,雖是一夜未眠,那種無與倫比的成就感卻足以讓我興奮良久。
弟子中具有「牛馬」精神者也是不勝枚舉,像三、四十年前,心平從清理環境到印刷傳單,辦事之謹慎,顯出他老成忠厚的特質,直至擔任佛光山住持之後,因積勞成疾,圓寂往生為止,種種行儀見證了「欲作佛門龍象,先作眾生牛馬」誠非虛言;慈莊在寺院裡從掃地抹桌到推銷書籍,無一不做,如今憑著流利的外語及親切的風儀,拎著一個小布包,獨自一人走遍天涯海角,建寺安僧;慈惠出家之後,赴日留學,每年寒暑假仍不忘回山幫忙寺務,數十年來以文教弘法聞名於海內外佛教界,四所大學籌辦工作效率之高,也令大家讚歎不已;慈容從幫我帶領幼稚園的小朋友做起,種種活動無一不與,近十年來在世界各地成立國際佛光會,對於教會事務的嫻熟,同儕中鮮有出其右者;慈嘉從香燈行堂到燒水洗碗,包辦一切雜務,其教課認真,學問紮實,說明了從日常作務中磨鍊心志,在胸膛間自然流露出來者,方為真才實學;心定在開山期間搬砂挑土、鏟地推車,有求必應,從不推辭,兩年前他被推舉為佛光山第六任住持,實是眾望所歸;餘如依空、依淳,大學畢業之後來山出家,也都是從擔任知賓及端茶服務開始做起,他們分別在日本東京大學及文化大學佛學研究所深造期間,還參與文化編輯工作,學成後受命掌管《普門》、《覺世》的編務及普門中學的校務,如今久煉成鋼,成為文教界的尖兵,這一切都是他們從辛勤作務中結成的花果。
佛光山在短短三十年間,之所以能有現在的規模,是許多人「作牛作馬」,服務大眾得來的成績,我絲毫不敢以「龍象」自居。隨著時代的進步開放,佛門僧伽的數量普遍提昇,這本來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但目睹許多人出家之後,即高高在上,自稱「僧寶」,藉「自修」之名,懶於說法,懶於度眾,懶於活動,懶於利生,長此以往,不僅是個人的墮落,也有違於佛教的真義。社會上也有許多人只知道坐享其成,一旦失敗,就怨天尤人,甚至為了名利虛榮而作奸犯科,結果一失足成千古恨。在此奉勸大家不要只看到別人的開花結果,要知道最初的播種耕耘是十分重要的,所謂「想要千人頭上坐,先在萬人腳下行」,唯有先作眾生的「牛馬」,才能成為頂尖的「龍象」。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