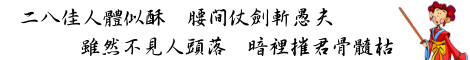往事百語2 -- 老二哲學 星雲法師著
向自己革命
| [日期:2008-05-30] |
作者:星雲法師著 |
閱讀: 次
|
一九五三年,我在撰寫《釋迦牟尼佛傳》時,常常被佛陀大公無私的精神所深深感動而熱淚盈眶。尤其了解佛陀一生的行誼之後,我知道佛陀不但是一個教育家、宗教家,還是一個革命家。不過佛陀的革命不同於世間上一般的革命家,一般革命家的革命,我稱之為「向外革命」,佛陀的革命是「向內革命」,也就是「向自己革命」──降伏自身生老病死的痛苦及心中貪瞋愚癡的煩惱。「向自己革命」這句話從此就成為我一生奉行的圭臬。
世間上的革命有很多種,有政治上的革命、社會上的革命、經濟上的革命、習俗上的革命、種族上的革命……。一個新朝代的誕生、一個新國家的成立、一個新主張的宣誓、一個新君主的登基,往往都是經過一番革命而產生的,但人事無常,法久生弊,等到時間一久,理想變質了,主義不實施了,又再需要另外一番的革命。俗謂「窮則變,變則通」,佛教也說「法無定法」,一切都是應時應機,世間法沒有一成不變的,有形的革命與無形的革命在世間上也就不斷發生,從而促使了文明的進步。
政治制度由君權時代進步到民權時代固然需要革命,社會型態由家族社會進步到宗族社會,經濟體制由農牧經濟進步到工業經濟,也都需要經過革命的歷程。革命本來是把一些迂腐、陳舊、罪惡、保守的思想、行為或體制予以革故鼎新,像中國武王伐紂的革命、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的革命、歐洲的新教革命、法國大革命、文藝復興革命、美國獨立革命等等,不但為人民帶來了希望的曙光,而且將國家社會,乃至思想信仰帶入嶄新的階段,為人類歷史寫下輝煌燦爛的篇章。但其中也有許多人以革命為藉口,逞一己之私欲,以眾欺寡,以強凌弱,結果使得萬千生靈不但未蒙其利,反而先受其害。這是因為人們的心中有貪欲、瞋恚、愚癡、嫉妒、邪見等許多不好的念頭存在,所以即使最初用心良善,但是當境界來臨的時候,就很容易被牽著鼻子走。因此,最究竟的革命應該是「向自己革命」。
如果我們翻閱史冊,將會發現一般的革命家大多是因為感到自身不自由、不安樂,進而聯想到別人的不自由、不安樂,才起來推翻不合理的勢力,這是一種由下而上的革命,是向別人革命,而非「向自己革命」。唯有佛陀是由上而下的革命,是「向自己革命」。他本來貴為王子之尊,過著優裕的生活,照理說是用不著革命的,但他看到許多遭受壓迫的民眾,為了公理和正義,因此奮勇地擺脫王子的虛榮,用一切眾生平等的真理來為那些被壓迫的階級打抱不平;他也看清了每個人心中自私的小我正是煩惱痛苦及世間鬥亂的根本,所以毅然地「向五欲榮華富貴革命」,捨離一切愛染執著,以求得真正自由自在的解脫。
由於佛法教人要「向自己革命」,因此,佛教流傳到世界各地,不但沒有發生過流血「革命」的事件,而且還能夠融入各種習俗,豐富當地的文化;佛教歷經不同的時空,不但未被時代的浪花所淘汰,而且還能夠因時制宜,破除妄執,繼續為每一世代的眾生作出最大的貢獻。
像大乘佛教代替部派佛教而興起,如果不是龍樹菩薩、提婆菩薩打著「性空緣起」的旗幟,「向保守的教團革命」,佛教那裡能再顯欣欣向榮的生機?如果不是無著菩薩、世親菩薩揭櫫「萬法唯識」的主張,「向頑空的思想革命」,佛教「真空妙有」的思想那裡能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揚?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如果不是道宣律師極力倡言「四分律五義通大乘」,積極推行「一乘圓頓妙戒」;如果不是百丈禪師進一步本著直下承擔「捨我其誰」的理念,超越戒律條文,創立叢林清規,那裡能像世間的「革命」一樣,以雷霆萬鈞之勢,讓中國佛教開創新的里程碑?若稱大乘八宗為當時思想上的革命者,實不為過也。至若南泉斬貓、丹霞燒佛,是為了「向舊有的包袱革命」,而不得不採行的激烈手段;慧遠大師的「沙門不敬王者論」,慧實大師寧受杖責,不向王權低頭,則展現了佛教高僧不惜身命,「向威勢強權革命」的本色;民國初年,太虛大師越挫越勇的無我表現及仁山法師大鬧金山寺的豪邁氣度,更是發揮了佛教大破大立的「革命」精神,否則,中國佛教會何由誕生?
然而卻有許多人只看到佛教因「革命」而帶來的發展,卻沒有看到祖師大德「向自己革命」的過程,像龍樹、提婆都有過一段荒唐狂傲的少年時期,但他們經過法水的洗禮之後,翻然悔悟,精進道業,學有所成,因此能在眾說紛紜之際,發出獅子般的吼聲,威服群倫;無著、世親本來都是小乘部派著名的論師,但他們在聽聞大乘佛法之後,覺昨日之非,而虛心學習,所以能進步神速,一日千里,對佛教作出卓越的貢獻;百丈懷海參學多日,被馬祖道一捏痛鼻子之後,才開悟見性,及至晚年,仍勤勞不息,躬自作役,他的魄力與擔當非一般匹夫之勇所能比擬;南泉普願用心習律、學教、參禪,而後心有所得;丹霞天然本欲進京趕考,在聽聞「選官不如選佛」一語後,及時覺醒,拜師學佛,終成一代大師;太虛大師曾掩關閱藏,而有悟境,又廣讀世間書籍,學通內外,而有改革佛教積弊的主張;仁山法師曾在金山寺窮研經典六載,並屢遊諸方,遍禮名山,而有拓落恢宏的思想。古聖先賢若非先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勇氣,放棄小我私利,如何能秉持大無畏、大精進、大忍辱、大慈悲的精神,坦坦蕩蕩地面對威勢利誘?
我最初也是心外求法,覺得別人都不好,只有自己才對。一九五四年元旦那一天,我翻閱過去的日記,發現都是在嫌別人如何不好不對,突然對於自己醜陋的心態感到慚愧。「為了向昔日的自己革命宣戰」,我不惜將數十本從大陸帶來台灣,寫了十多年之久的日記付之一炬,經過這麼一燒,對自己的愚昧,方才有一點點覺醒,不禁回想起自己過去所從事過的「革命」事蹟:
二十歲那年,我踏出佛教學院大門,身處局勢動盪不安及佛教地位低落的年代裡,眼見社會種種的危難,耳聞眾生痛苦的呼喊,我也像許多熱血澎湃的僧青年一樣,擁有滿腔改革佛教的抱負,有鑑於太虛大師的教產、教義、教理「革命」,因為沒有自己的地盤,以致功敗垂成。所以我與同道們欣然接受南京華藏寺,並且訂定新生活規約,試圖藉此恢復叢林學團的道風,然而這豈是一個經懺道場所能做到,失敗自是在意料之中,這是我生平以來第一次的「革命」。
一九四九年,來到台灣之後,才發現此地佛教地位更是低落,許多佛寺被軍營軍眷所佔住;耶教可以公然到寺院傳教,散發傳單,但對於佛教的弘法活動卻多所限制;至於社會人士謗佛毀僧的言行更是不勝枚舉,報紙、電台、電影、小說,甚至教科書中,都有曲解佛教的地方,當時正值戒嚴時期,佛教徒們大多像驚弓之鳥,連自己是佛教徒都不敢承認,遑論挺身而出,護法衛教。許多人說這是因為民眾多隨政商人士信仰耶教有以致之,我卻認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佛教徒具有「向自己革命」的決心,將本身的思想、行為健全起來,積極弘法利生,努力為民謀福,才是振興之道。
一九五二年,當我以二十六歲之齡,當選為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時,為了替有為的僧青年在教會中爭取一席,以期會務更有朝氣,進而促使佛教的迅速發展,我多次直言不諱,抨擊長老把持教權,應及早退休。自己一無建樹,卻想先反對別人,這樣的「革命」當然注定是要失敗的。
是年五月,我應邀駐錫宜蘭雷音寺。由於來台數年之間,目睹佛教徒佛道不分,只知趕赴齋會,祈求福壽,卻不知佛法真義,遑論內修外弘,對此我早已感慨於心,這時又見到寺院佛殿內供奉了一百多尊神像,自忖正好可以藉此教育信徒,遂將其全部收藏起來,只供佛像,以正視聽,此舉雖然觸犯部份地方人士的習慣,幸好我也另有基礎,所以才沒有被人打倒。這一次「革命」的小小勝利對我不無鼓舞之效。
後來,為了出外佈教,屢被干涉,我前往治安部門據理力爭;為了運用現代聲光器材弘法被警察取締,我也與有關單位周旋到底;對於名伶顧正秋在永樂戲院唱戲誣衊佛教,我致信抗議;對於越南總統吳廷琰迫害佛教,我也撰文筆伐。儘管長老、信徒反對我提倡以歌聲弘法,並且以殺害為恐嚇,我仍然義無反顧,不為所動;雖然數十年來,中國佛教會以我為假想敵,對我種種牽制,甚至在開會時,公開議論要如何來打倒我,我也依舊勇往直前,為所當為;一九七三年,我想要成立中國佛教青年會,曾驚動了當時主管宗教部門的蕭天讚先生,他親自上佛光山,要我取消申請,我雖迫於情勢,不得不依命行事,但我仍能於數年之後,在世界各地成立國際佛光會……。在親身經歷了這許多佛教制度思想的革命之後,我慢慢地發現自己也和世間上的政治家、社會家一樣,向別人「革命」總不可為也,最好是先「向自己革命」,先去除自己的我執、法執,方足以自利利人,廣度眾生。
像我初來台灣弘法時,對於此地迷信的習俗深不以為然,但是後來漸漸發覺信仰是有層次的,就好比學校分有小學、中學、大學,我何必對每一位初入學的人要求如此嚴厲呢?其實,迷信比不信要好,回想過去大陸鄉村方圓幾十里沒有一間派出所,維繫治安的也往往只是一間寺廟,任何人有了紛爭,只要雙方當事人在神佛面前發誓,就得到解決。由於大家具有「舉頭三尺有神明」的觀念,不敢為非作歹,所以能相安無事。這說明了迷信也有其效用,比起什麼都不信,或誤信邪教,迷信至少還有維護善良習俗的貢獻。更何況在佛教的歷史上,玉皇大帝、財神爺、城隍爺、關雲長等都是護法神祇;大陸上的佛教學院也經常收留道士就讀,我何不效法古聖先賢,秉持包容與尊重的理念呢?經過一番心理上的「自我革命」之後,我一改過去二分是非的看法,進而從內到外開拓了更寬廣的空間。所以早年我設立的念佛會,往往都是先借用神道的寺院成立,大家和平共存,友愛協助,為宗教融和添增佳話。我也曾到指南宮參觀掛單,並在祈夢室上睡過一宿;甚至我創立的南華大學,所聘請的首任校長就是研究道教多年,曾任道學院院長的龔鵬程先生。自弘法以來,我曾到新竹城隍廟多次講經開示,也曾遠赴馬來西亞天后宮多次主持法會。我不但到過北港媽祖宗聖台弘揚佛法,而且幾十年來,我一直想寫一首讚頌媽祖的歌詞,雖已醞釀多時,可惜尚未完成。
過去在大陸參學時,雖然生活貧困,經常穿著滿是補丁的衣襪,但保持整潔威儀始終是寺院叢林的法師們對自己最起碼的要求。來到台灣,我卻看到僧侶們足穿木屐,頭戴斗笠,身著短衫,手撐雨傘,心中十分不能接受,甚至有些出家人似乎忘了自己是人天師表,不但手拿包袱,滿街奔走,而且購物還價,爭先恐後。目睹於此,更是痛心疾首。為了向生活的陋習挑戰,我不但在佛教雜誌上多次撰寫有關四威儀的文章以資提醒,而且在成立佛學院之後,便訂立規約:不穿長衫,鞋襪不整齊,不可以出門;非滂沱大雨,即使烈日當空,也不准攜帶雨具。現今各個佛寺道場對於叢林生活禮儀逐漸講究重視,我雖不敢居功,但起碼證明了:「革命」不一定要求別人,從「自己」先做起,會收到更大的功效。
早年曾經有一段時期,我常到富家信徒應供。有一次,台灣警務處處長陶一刪先生曾辦一桌素齋,與我對談,餐畢之後,又用豪華轎車送我坐頭等火車。到了高雄下車的時候,我突然心有所悟,對於自己這種貪慕虛榮的心理感到極為憎惡,為了徹底地「向自己的貪念革命」,從此我經常到鄉間小徑,偏僻村莊佈教,像旗山、美濃那一帶的山地,在光復初期,我不知來回多少次;東勢、后里、銅鑼、火炎山,也是我經常路經之地;甚至八仙山、太平山都有我行腳的足跡。就這樣,我終於逐漸走出我心內的佛光山來。
我年輕時,非常看不起人前人後兩面不一的假道學,及掛羊頭賣狗肉的偽君子。尤其事關佛教時,我往往不惜與人抗爭。例如:為了智光商職,我曾和南亭長老爭執;為了《人生雜誌》,我曾和東初法師辯論;為了教會制度,我也曾和白聖法師多次議論,常常都是弄得不歡而散。後來我自覺雖是理直氣壯,但也未免過於剛直。有感於此,所以後來我到處設立托兒所、幼稚園、兒童班、星期學校,希望從幼兒的慈愛做起;我也走遍城市鄉野、神廟廣場,給人佛法,施予信心;甚至我跑遍台灣全省的大小監獄及離島的看守所,期能藉此讓不幸誤入歧途的人獲得重生。現在我經常自豪地向徒眾們說:「我在台灣五十年,從來沒有對信徒動過瞋心,從來沒有罵過一個信徒。」想當初如果不「向自己的瞋心革命」,何能致此呢?
我的朋友當中,煮雲法師最沒有嫉妒心,是我等最好的模範。他對於任何人一點點好處,都讚歎隨喜;他對於任何人一點點成就,都恭維羨慕。每當受到嫉妒我的人給予我無情的傷害時,想到他的寬容無爭,總是令我慚愧不已,既而捫心自問:「難道我不曾嫉妒過別人?難道我不曾在無意中傷害過別人?」從而砥礪自己:「爭氣,不要生氣;好強,但不逞強。」後來,我不斷提倡「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精神,並且身體力行,不曾間輟。多年來,雖譏毀不斷,但我仍能心存仁厚,不予計較,甚至因此而化敵為友,轉危為安,當初能「向自己革命」,誠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回首來時路,無時無刻不是在兢兢業業中防範身口意業的過失,深深感到心中八萬四千種煩惱猶如八萬四千個盜賊,一不小心,便會落入它們的牢籠之中,難於出離。所謂「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將軍主帥能行令,不用干戈定太平」,我們唯有自己不斷地提起正知正見,不斷地「向自己內心的煩惱盜賊革命」,不斷地改心、換性、回頭、轉身,不斷地自我尊重,自我肯定,才能如古德所云:
幾年鏖戰歷沙場,汗馬功高孰可量?
四海狼煙今已熄,踏花歸去馬蹄香。
「向自己革命」能夠勝利,是多麼美妙的世界啊!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