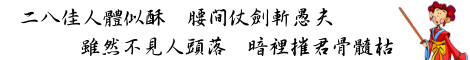往事百語3 -- 皆大歡喜 星雲法師著
錯誤不能一直下去
| [日期:2008-05-30] |
作者:星雲法師著 |
閱讀: 次
|
記得二十多年前一次法會的前夕,我到會場巡視,發覺所有的設計、佈置都不合理想,便將主事的弟子叫來問話,她皺著眉頭表示:「明天法會就要開始了,無法再作任何改變。」我當下責問他:「妳要知道,錯誤不能一直下去!」結果大家連夜拆除,重新佈置。第二天,人人稱讚會場莊嚴殊勝,有如靈山再現。弟子伏首認錯,對我說道:「還好是當初師父的一句『錯誤不能一直下去』。」「錯誤不能一直下去」不但是我經常拿來課徒的警語,也是我一生處事的原則。
許多人覺得一點點的錯誤,何必那麼斤斤計較?其實,小「錯誤」如果任意不管,就會鑄成大「錯誤」。過去有一個死囚在臨刑前,要求吸吮母親的奶水,當母親解開衣服時,他一口咬下母親的乳頭,憤憤地說道:「小時候我偷了別人的東西,妳不但不罵我,還誇我聰明,現在我到了這個地步,都是妳造成的!」這則耳熟能詳的故事無非告訴我們:小「錯誤」也要注意,否則「一直下去」,將會貽害終生。歷史上,如戰國時代,燕國由於中了田單的連環計,一戰而潰;趙王因為聽信謠言,不顧眾人的勸諫,陣前換將,讓僅知「紙上談兵」的趙括率軍攻秦,結果一敗塗地。目前的社會新聞中,像不久前,台北捷運局因為一個小小的匣門沒有鎖好,使得兩名孩童觸電喪生;某街道一個小小的坑洞多日來沒有修補,以致經常發生車禍,造成人命的傷亡。凡此都說明了:因循苟且,「讓錯誤一直下去」,足以釀成不可彌補的災禍。
其實,「錯誤」具有教育的功能,但關鍵在於我們是否搪塞諉過,讓它「一直下去」?像唐太宗因為具有「錯誤不能一直下去」的決心,察納雅言,從善如流,所以成就了無可匹敵的大唐盛世。羅斯福總統也是以坦承己過而著稱政壇,在他還是紐約市長的時候,曾面對大眾,訴說自己因一時不察通過議案,結果贏得了更多人的尊敬。高僧大德中因糾正過失而開悟見性者更是不乏其人,像德山宣鑑禪師因為答不出賣燒餅老婆婆的問題,知道自己所知有限,為了「不讓錯誤一直下去」,即刻將自己所著的《青龍疏鈔》燒毀,繼續參學,終於在龍潭禪師座下悟道;白雲守端禪師因為老師的一句「你連一個臉色都放不下,還不如廟前耍猴把戲的小丑」,而心生慚愧,努力參禪,因為他能秉持「不讓錯誤一直下去」的毅力,時時注意自己的舉心動念,所以也獲得了開悟。可以說,綜觀世界上有成就的人,都是因為對於自己一點的「錯誤」都不肯放過,所以能日新又新,不斷進步。
我從小因為做事也力求完善,所以經常獲得親友的稱讚,不料出家之後,卻經常遭到家師無情的斥責,剛開始時也曾覺得百般委屈,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恍然大悟:家師之所以採取「以無理對有理」、「以無情對有情」的方式來教導我,是希望我能秉持認錯的態度行事,不要像一般人一樣犯了「死不認錯」的毛病。後來,我一生走來都十分注意通盤考慮,「不讓錯誤一直下去」,對於日後的弘法事業產生莫大的助益。
我二十歲時,從佛學院結業出來,曾極力主張僧伽也要加入社會生產工作。來到台灣之後,聽到慈航法師對我開示時說:「僧伽出家是要立志作人天師範,如果也要開工廠,難道要作工人嗎?如果也要開商店,難道要作商人嗎?……」
我聞言若有所悟,知道「錯誤」的宣導「不能一直下去」,當即發願:「我所要從事的生產工作,是要為信徒生產正信,為社會生產感恩,為大眾生產善緣,為國家生產慈悲,而不是生產工人、商人……。」後來我開創佛光山,訂立「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為開山宗旨,並以「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為佛光人工作信條,實際上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萌發意念,再經過多年以來的醞釀所產生的。
要做到「不讓錯誤一直下去」,除了必須接受別人的勸告之外,能夠時時反省,自我觀照,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佛陀不但經常強調自覺覺他,而且教導我們要以達到覺行圓滿為修行的最高境界。像中國南北朝時代的道生大師,不惜身命,提出「一闡提也能成佛」的主張;泰國的蒙昆貼牟尼法師不懼迫害,以自己修持所證,倡導「法身」的理念,就是在秉持「不讓錯誤一直下去」的精神,讓佛教的真理得到高度的發揚,以裨益更多的眾生。
我雖無古聖先賢的通達智慧,但有幸蒙受叢林大海的陶鑄,歷經大時代的變遷,在一番身心洗練之後,我逐漸釐清佛教未來的方向,立志效法六祖惠能大師和太虛大師所提倡的「人間佛教」思想,破除積弊已久的觀念及措施,「不讓錯誤一直下去」!在諸多佛教革新的事件當中,尤以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仁山長老為革新佛教而大鬧金山寺的事件最為大快人心,因為此舉促使中國佛教會催生成立,讓風雨晦暗的佛教出現了一絲曙光。直到中日戰爭之後,當我等五位焦山佛學院的青年學生被推選列席旁聽中國佛教會的會議時,我的心中即刻為之一振,以為施展抱負的時機終於來臨了,不料時局生變,未能實現理想。
及至來台,中國佛教會在台復會,我仍積極參與會務,只可惜主事者只顧擴張自己的教權,致使教會無法發揮功能,我想結合有志之同道另組教會,但時值戒嚴時期,政府當局以與人民集會條規不符、佛教已有教會等諸多理由不予准許。儘管困難重重,我依然多次據理力爭,因為我覺得:雖然有了縱貫公路,還是可以架設高速公路、舖設火車鐵軌、開發捷運系統,因為這些設施不但不會妨礙原有道路,而且能為大眾提供更多的便利。所謂「條條大路通長安」,多一些管道,多一些流通,不是很好嗎?進步的國家都怕一黨獨大,招致腐敗,為什麼民間的教會團體卻不能多設幾個呢?基於「錯誤不能一直下去」,雖然「中國佛教青年會」、「中國佛教會」的理想力爭無效,我還是念茲在茲,終於在一九九一年獲得大家的共識與認同,成立了「中華佛光協會」,翌年在洛杉磯成立「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目前除了協、分會遍布全世界之外,還有青年團、童軍團等單位,會員們在各地不但凝聚力量,融入當地社會,發揮融入本土的理念,而且在淨化人心方面也不遺餘力,各種文教活動多采多姿。但我並不因此自滿,仍經常召開會議,檢討會務,因為我確信:唯有不斷改進,「不讓錯誤一直下去」,才能不斷更新,不斷成長,自利利他,福利社會。
剛來到台灣的時候,看到當地佛教落後的情形,回想過去大陸叢林參學的盛況,曾以「回憶比現實美麗」為題撰稿,抒發撫今追昔之感慨。當這篇文章發表在《人生雜誌》,再度映入我的眼簾時,卻不禁感到赧然,自覺回憶雖然能夠作為借鏡,但一味沉湎其中,就如同「白頭宮女話當年」一樣,也是「錯誤」的,「不能一直下去」,不如改善現況,前瞻末來更有意義。
當時民風保守,再加上長久以來,「山林佛教」的型態深入人心,佛教成為一種老年人的宗教。因為出了家之後,沒有什麼事情可做,許多有知識,有抱負的青年僧尼因為不甘願將歲月消磨在早晚課誦及打掃環境之中,只有易裝再入社會;一些在家的佛教青年男女起初也是滿懷虔誠悲願,皈依三寶,希望能為佛教,為眾生奉獻一己之力,但法師們除了教他們拜佛、念佛以外,沒有餘事可做,最後也只有隱遁山林或離開佛教一途。目睹佛教留不住人才,庸才方能在佛教生存,我深深感到:這種「錯誤」的接引方式如果「一直下去」,將使得佛教益加衰微,遑論光大佛教,弘法利生!
因此,我不但大聲疾呼,籲請佛教的長老們愛護青年,創辦佛化事業;自己也身體力行,即使在生活最艱困的時候,仍節衣縮食,將所有的齋供、嚫錢拿來作為維持佛教事業的經費,結果佛教事業,如文化、教育、慈善等,不但利益了社會大眾,也為佛教培養了許多人才。例如,籌設佛光大學和西來大學的慈惠、在世界各國設立寺院的慈莊、慈容,都是當初佛教文化服務處的基本幹部;為我在幼稚園、育幼院帶領小朋友的依來、蕭碧涼等,都成為傑出人才。幫我辦理佛教學院的慈嘉、依空、依恆、依淳、依華、依法、慧開、慧寬等,都是由於佛教事業而接引他們進入佛門;現時在世界各地建寺的依寬、慧禮、慧應、永祥、永全、滿禎、覺穆等,也成為經驗豐富的工程專家;在朝山會館、麻竹園、雲居樓服務的蕭慧華、黃美華、吳秀月、妙晉等,都因展現了行政管理的才華,而被大眾推選為佛光山宗務委員的候選人;曾經擔任典座的依恆、依果、永度、永均等多位弟子,現在也住持一方,領眾薰修。在出版事業、編藏及書記室工作多年的慈怡、依晟、永明、永進、永莊、滿光、滿濟、滿果等人,則是推動現代佛教文化發展的功臣。
事業固然具有養眾、教眾的功能,但如果沈溺其中,只知向前奔馳,不知向後觀照,行之久矣,也會發生「錯誤」。所以數年前,我陸續闢建關房、禪堂、淨業林、禮懺堂,好讓徒眾們在工作之餘,輪流靜修,但規定修持階段到了一定的時日,就必須出來為大眾服務,因為養深積厚,充實自我雖然是重要的,但是身為佛子,如果不能將修持帶到日常生活,不能將修持運用在工作上,甚至不能將弘法視為自己的家務,不能將利生當成自己的事業,就是「錯誤」的。
過去常聽人說:「中國人像一盤散沙。」佛教的情形也是如此,我在年輕的時候,就時時思考其中的原因,後來發現這是由於長久以來,中國人,尤其是佛教徒,不知道組織的重要,不強調制度落實才有以致之。其實,在佛陀時代的僧團就是一個講究現代化的組織,它的布薩舉過制度,它的羯磨議事制度,甚至比現代國家的法律程序還要來得細密周全;它通達人性的管理方式,它權巧變通的律儀規章,也足以媲美當今任何的團體機構。可惜的是,後代的佛子不知道靈活運用,擴而充之。所以,雖然歷史上曾有高僧大德如道安、百丈等人融古匯今,編纂僧尼軌範,撰修叢林清規,但終因後繼無人或宗派分歧等因素,不能流傳久遠。
「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同樣的,沒有組織制度,如何凝聚成員的力量?有鑑於「錯誤不能一直下去」,我在早年成立念佛會,在壽山寺時,就著手擬訂寺院規範組織及辦法章程,後來闢建佛光山,更大刀闊斧地建立制度法規,並藉此剷除教界一些似是而非的觀念,例如:修行人擁有日用物資雖然不是罪惡,但如果不能清貧守道,乃至遭致譏嫌,就是「錯誤」的。所以,佛光人不准戴台幣二千元以上的手錶,不可用台幣五百元以上的念珠,不准私置產業,不准私蓄財物。化緣如果能化到對方的歡喜,化到大眾的善緣,固然是一件美好的事,但如果僧眾不憑自己的智慧道德苦勞犧牲來奉獻眾生,卻先想到別人的供養恭敬,從而損失了佛教的尊嚴、佛教的公益,就是「錯誤」的。所以佛光人不准私自化緣、不准私建道場、不可以經懺化緣為事業。度人出家固然功德無量,但如果濫收徒眾,致使僧團水準降低,甚至造成徒眾各自衛護自己的師父,鬧得人我是非烏煙瘴氣,就會變成嚴重的「錯誤」。所以,佛光人不准私收徒眾,不准私交信徒。人才派到外地駐守,固然可以多方學習,但如果放任不管,任其行事,也是「錯誤」的,所以佛光山實行輪調及巡監制度。
所謂「會得香雲蓋,到處吃素菜」,經懺佛事本來是佛教了生脫死,弘法度眾的法門之一,長久以來,卻因為維生容易,而成為一些僧侶的職業。眼看不知多少出家眾埋沒大志,墮落僧格;多少社會人士誤解佛教,喪失道心!在深惡痛絕之下,我決定從自己做起,「不讓錯誤一直下去」,所以凡有人要求我做功德佛事,一定要先成為我的會員或佛教信徒,否則我都堅持拒絕,甚至為此不惜得罪名門大戶。但久而久之,我發現經懺佛事雖然行久弊生,卻也有其存在的理由,因為每個人根性不同,有些信徒可以一輩子不聽經聞法,但是百年之後,卻不能不找法師念經超薦;有些信徒可以在平日不參加法會誦經,但是在喜慶節日,卻一定要延請法師念經祝願;甚至有些人任你舌燦蓮花,講盡了佛教的道理,他也不信,但是參加了一場功德佛事之後,立刻就被莊嚴的壇場所攝受而皈依三寶。自忖:對於經懺佛事如果一味抱持禁止的態度,徒然失去了度眾的方便,也是「錯誤」的,所以後來我訂出一套程序、辦法予以淨化改善,並且一再告誡弟子們,要讓經懺佛事做得莊嚴如法,而不以熱鬧應酬為能事;要讓經懺佛事作為和信徒結緣的方式之一,而不流於世俗經營;要讓經懺佛事能真正地超度亡者,安慰生者,成為一種了生脫死的修持,而不是虛假的應赴;要讓經懺佛事促使大家了解佛教對日常生活的美化作用與實用價值,而不只是死後的追思。
三、四十年前,佛寺爭相舉行法會,但都是以誦經消災、聚會吃齋為號召,徒有「法會」之名,而無「法會」之實。因此,我除了在例行法會中添增說法項目之外,更應當時信徒的喜好需求,到處成立念佛會,在共修中兼帶講經,一方面讓大家知道佛教的好處,吸引更多的人前來學佛;另一方面藉此提高佛教徒的水準。不久,佛教果然適應大家的根機,逐漸興盛起來。記得當時我曾有一理想:「希望將來有一天,世界各地的信徒都能在週末同一時刻,同聲念佛。」
二、三十年後,這個願望果真實現了,我卻又在佛光山開會中提議:「為大眾在週末假日籌劃多樣化的弘法活動。」有些弟子不能了解,前來問我:「師父!週末同時同聲念佛,不是您過去以來一向的理念嗎?為什麼突然要改呢?」我回答他們:「因為時代不斷地變化,念佛會有其時代的意義及功能,在目前多元化的社會裡,如果我們依舊以過去的方式一成不變地推行念佛共修,就是『錯誤』的!」
一九九七年,佛光山封山之後,首度推出「假日修道會」,列出禮懺、禪坐、念佛、朝山、抄經、齋戒、佛學講座、頭陀義工、親子營、青少年營等十種修持方法,供參加者選擇,就是一種嚐試性的突破。從目前教育界、軍警界、政府官員、醫護人員等紛紛組隊報名參加的情況看來,當初的決定是正確的,從而更加警惕自己:「無論是個人或團體,無論是內修或外弘,固步自封,墨守成規,都是『錯誤』的,『不能一直下去』,我們必須像海水一樣,時時激盪,時時更新,才能具有充沛的活力。」
舍利弗曾經問佛陀:「為什麼您制定的戒律,有時開,有時遮呢?」佛陀回答他:「這是為了因時制宜,因為有些事情,在此時應該要這樣做,在彼時必須要那樣做。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把握自利利他的原則來行事。」又說:「我所制訂的戒律,如果在其他地方不宜實施,就不要實行。」偉哉佛言!什麼事該不該做,必須因人、地、時、物等背景的不同而有靈活變通,否則也是一種「錯誤」的繼續,為害或許更深。例如:慈悲為懷是對的,但如果放縱歹徒,姑息養奸,就是「錯誤」的;隨緣無求是好的,但如果喪失原則,不知變通,就是「錯誤」的;男婚女嫁是對的,但如果認識不清,勉強湊合,就是「錯誤」的;養兒育女是好的,但如果視為己物,任意處置,就是「錯誤」的;孝順父母是對的,但如果助其惡行,耽誤前途,就是「錯誤」的;廣交朋友是好的,但如果結黨組派,陷害他人,就是「錯誤」的;考試掄才是對的,但如果偏重成績,選人失當,就是「錯誤」的;出國深造是好的,但如果浮誇虛榮,不切實際,就是「錯誤」的。「錯誤」有時是因為自己的一念之差,有時是由於前人的偏差誤導,但無論如何,一旦發現了「錯誤」,就必須要以無比的決心及毅力,阻止它「一直下去」,唯其如此,才能圓滿自己的人生,促進社會的進步。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