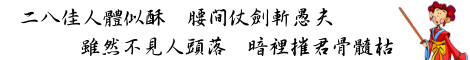圖/楊惠姍
楊惠姍,台灣七十年代的家喻戶曉演員,曾榮獲金馬獎及亞太影展最佳女主角。一九八七年,楊惠姍在事業的巔峰,毅然息影,投身中國現代琉璃藝術,與名導演張毅共同創立琉璃工房,苦心研究特殊的琉璃脫蠟精鑄法,先後在世界十數個國家展出,在國際藝術界引起很大的回響。她的作品富含傳統中國語言與人文思想,張毅為每件作品的題詩更如禪詩般的直指人心。
「楊惠姍.中國現代琉璃藝術展」上月中旬在香港太古廣場舉行,其中展出的「澆鑄觀音」系列,以嶄新創作概念詮釋觀音與佛的形象,由具體轉推成虛實並存,如夢幻泡影,觀眾看得讚嘆。
讚嘆的不光是楊惠姍的創作力與技巧,更且是作品所蘊含的「無相無無相」的境界,那是作者的自性流露,也是與觀眾以心傳心的無聲擁抱。

圖/楊惠姍作品
「我的第一個反應並不覺得難過,我真的沒有,我的反應反而是好啊,可能觀音菩薩覺得我做得還不夠好。」楊惠姍三言兩語,道盡了是迷是悟的人生道理。「確實做得不好,應該還要再好,只是沒勇氣把她推倒而已。」想開了,沒有執著已發生的事情,就覺得很舒服、很自由。
楊惠姍本想做一個大的千手觀音,卻受到一米高的爐子的限制,作品的體積大不了。這一下子觀音雕塑倒了,突然間思想也打開,「我幹嗎要被那個框框困著?要做就不要受爐子的限制。」
更大的爐子,表示要額外的投資,更長的製作時間。做爐子就要一年,進爐鑄造也要一年,而最後燒出來的作品,其成功率只有15%,划得來嗎?
「花錢、花時間,這個不成,那個不划算,這樣想的話,只是一盤生意。」而楊惠姍是搞藝術的,並非做生意。
主動掌握自己的生命
從名演員到琉璃藝術家,沒有任何學院訓練的背景,只憑自學的無比毅力,楊惠姍走出了一條別人想也不敢想的艱苦道路。
「拍戲到了後期,內心很不安,三十幾歲的女人,演藝生涯是往下的,但我覺得那時候的生命是最好的,各方面比年輕的時候成熟,學習的慾望比年輕的時候強。而我發覺電影給我的學習已經不夠了,我要花很多時間去等一個好的導演、好的劇本、好的老闆,這個等待用了太多的時間,我覺得應該要積極一點、主動一點去掌握自己的生命,所以我與張毅在想,除了電影,我們可以做甚麼?但這個事情一定要跟創作有關。」這兩口子認認真真的花了很多時間去尋覓、探討、研究要開拓甚麼事業。
上天似乎為她的「事業轉形」做了妥善的接口,楊惠姍與張毅導演拍攝最後一部電影《我的愛》的時候,片裡用上很多琉璃作道具,令楊惠姍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從來沒有想到琉璃可以做藝術作品。它的創作空間很大,一般的素材質地只能做平面的東西,可是琉璃可以看到裡面,而且它的色彩、質感的豐富性,可以燒成不像琉璃的感覺,可以是石頭或任何的東西,有趣極了!」
張毅也喜歡琉璃,兩個對琉璃一無所知的人,就憑著熱情與蠻勁開始起來,「當時沒有很多的想法,反而以前花了很多時間去想的計劃,後來都沒有做。越想得多越越害怕,越不敢做。」
開始「琉璃人生」以後,想像不到的困難排山倒海,「我們就是找一些資料、一些書,好像學做菜一樣,當然比做菜複雜困難多了。琉璃藝術牽涉的材料比較多,不純粹是琉璃,過程裡面還要跟很多材料一起,如蠟,silicon,很繁複,這都是我們在做以前沒有想到的。」
「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身如琉璃,內外明徹」
三年前,楊惠姍嘗試複製鑄法的佛像主題作品,結果成為楊惠姍最多的創作主題,琉璃的材質的特色,更是十分巧合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質地。『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裡云:「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身如琉璃,內外明徹」,佛經的說法,使「琉璃」的物質色彩多了一層精神意義,讓傳統的佛像琉璃化,結果成為楊惠姍琉璃創作的方向。現在她許多佛像作品已成為很多佛教徒的念持佛,在燈光裡,琉璃佛像彷彿透明無重的羽化狀態,呈現了一種特殊的冥想空間。
日本奈良的國寶級寺廟藥師寺內寫經堂,供奉了楊惠姍的作品「藥師琉璃光如來」。當楊惠姍親自把作品送到藥師寺,寺院的僧人莊嚴恭敬地對這件作品頂禮參拜。
「在那一剎那,內心有一點不能承受,我畢竟是一個很普通的凡人,做了這尊藥師佛,看見寺廟住持等虔誠地向著頂禮,內心實在有點不安。後來作品放在抄經堂,信徒進入時都要向他禮拜,我也不例外,那時候,我覺得那不再是我的作品,心也放開了。」
很多人問她,好不容易十月懷胎似的把「孩子」誕生下來,捨得把「孩子」送走嗎?「做一件作品要花很多心力,時間很長,作品結束之後,我就不會再去想。」楊惠姍證入了佛教思想的當下,她享受的是創作的過程,她享受創作帶給她的挑戰與滿足,但沒有執著對作品的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