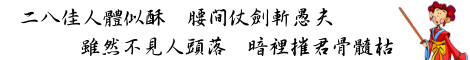圖/李娜
久違了,李娜!在望到她的那一瞬間,我的思緒不由自主地又回到了從前。那時她年輕,我對時間的感受也不如而今深刻;而今,當我獨處時,總是忍不住要問上一句:歲月遺留給我們的都是些什麼呢?
第一次見到李娜是在央視「難忘一九八八」晚會上,她像鳥兒飛過窗口一樣從我眼前掠過;以後的相見都是在舞台上下,在攝影棚內外的匆匆擦肩而過之中。她給我留下的印象深刻嗎?不,談不到深刻,只記得那雙與眾不同的眼睛,總是不願睜得太開,好像噙住了很多光線,以至於不願再釋放出來似的;對同行也是淡淡相處,正如歌曲裡所唱的「水中的一抹流紅」,她獨自而在,獨自存在於自己音樂的寧靜之中。
但是,一曲《青藏高原》令我對她刮目相看。不是嗎?在她並不高大的軀體內誰會想到竟然蘊藏那麼一種生命的原始的激情呢?聽,在盤旋而上好似直入雪峰純靜之廣袤的蓬勃旋律中,巨大的藝術渲染力驟然迸出,哪一個聽者的心靈能抗拒這一震撼呢?多少次,我沉溺在她用聲音製造的漩渦之中,在變化莫測的旋律中起伏,內心久久不能平靜。確切地說,我對《青藏高原》這首歌的喜愛,還有更深層的內涵,它不僅喚起了我對兒時在窮困的生活環境中去追求藝術之精神的那股執著的熱情的回憶,也使我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誠———因為,實在說,我到過青藏高原,我也在高原凜冽的雪風中站立過,也在向高原之魂朝拜的崎嶇道路上行走過,也被從石頭縫裡鑽出的搖曳著花鈴的小草感動過。是的,一株小草向大自然所展示的頑強不息的進取精神更能像征真實的生命,而今還是我藝術創造所取之不盡的源泉。正因如此,我才能體會到李娜是用怎樣的一種心靈去體驗去演繹她的「青藏高原」。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這首歌中蘊藏著某種接近於真實的精神內涵;我之所以說它「接近於真實」,是因為純粹的真實是不可能達到的,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走在一條通往真實的道路中。
以後,我聽說了她在香港的演唱時,以無伴奏的方式謳歌《青藏高原》。全場觀眾,鴉雀無聲,靜心地聆聽,是的,誰的心靈能不為那跟「青藏高原」一樣巍峨純淨的絕唱所感動呢?唱完了,李娜從自己的旋律中解放出來了,但觀眾還陶醉在她所製造的聲音的波紋裡,半分鐘的沉默等來了長久的掌聲與歡呼不斷———我想像得出那該是怎樣壯觀的場面。
後來,聽說她出家了。我———惋惜不已,而不解與疑惑,更伴隨了我不少日子。
終於,在洛杉磯,彷彿命運之神刻意安排的一樣,我碰上了她。
真的,她是出家了!
一身黃衣僧侶服,潔淨的剃度代替了當演員時頭上的髮飾;然而,面色紅潤,目光有神,某種純之又純以至於無塵的精神充溢在她的每一個舉動中。幾乎每個歌手必然會呈現在臉上的那種勞累的蒼白和缺乏睡眠的倦意在她這裡銷聲匿跡,連曾經在她眸子中閃爍過的懶散和迷茫也不見了;而今,出家的李娜全身蕩漾著一股「在家」的和諧與安祥,交談起來呢,卻滔滔不絕,一變她過去與任何人交接時那淡淡的似乎接近於冷的表情。
話題很快轉到我的網站上,她對此所表示的關心令人感動,我甚至覺得這可能就是最高層次的關心了,因為她根本就漠不關心,彷彿世界上並沒有網絡這回事兒。確實,我能理解,她把自己從真實的「網」中解放出來,其目的顯然並不是為了再進入虛擬的網中。但我還是徵詢能否為她製作網頁的事。她笑了:「我可能離那些太遠了,我都快被忘記了。不是被別人,而是被自己,我真的不記得十年前的那個李娜了!」我說:「你當然有忘記自己的權利,這表明你的修行又進入更高的境界;可你的觀眾,你的歌迷不會忘記,你的成就還被社會承認,這些不應該成為佛家『四大皆空』的理由吧!」她聽後,若有所思地說:「對以前的我怎樣評價,那是別人的事,也可以說是社會的事,我無暇去顧及,也不會去顧及。用句古人的話說就是『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了。至於製作網頁,那更是你的事,你怎麼幹我就不管了;我剛入佛門,得一心一意地學法護法。」我說:「是脫離塵世?」她微微一笑:「還沒有那麼玄,但總得進行研究和探討吧?」
她說得如此平靜,我聽得卻很不安寧。
我還不住地琢磨,為什麼找不到當年李娜在舞台上的影子,眼前的她———精神狀態不錯,紅潤的臉龐,自自然然地溢出顯然是得益於養身修性所至的那麼一種健康神色。我若有所悟:如果說舞台上的李娜是一枝掩藏不住自己芬芳的玫瑰,那現在的她就是一朵靜靜釋放自身清純的百合。一個人在自己一生中,能同時擁有這樣兩種截然相反的人生境界,還有什麼不可以滿足的呢?
和她一起來的是她的媽媽。母女倆站在一起,像一幀圖畫。不是出家人截斷六根,不應該有凡夫俗子那塵世間的兒女情長嗎?為什麼她還跟自己的母親在一起呢?是為了生活本身,還是某種感情的需要?———我克制不住自己好奇的衝動,由然迸出了所有人可能都希望向李娜提的一個問題:「你……你為什麼出家呀?」她微微一笑回答:「我不是出家,我是———回家———了!」她用拖長的音節來糾正我的問法,聽得出,她已經不止一次向別人回答過這個問題;現在連我這樣「高級」的人物也願意把自己降得如此「低級」,她顯然微有憾意。
許是看我心誠,她隔了一會兒便慢慢地向我道出自己是怎樣看破紅塵的:「我過去的生活表面上很豐富,可沒有什麼實質的內涵,不是嗎?唱歌,跳舞,成為媒體跟蹤的對象,這幾乎是我過去生活的全部內容……多早啊,就身不由己地進入了名利場的追逐之中。每當獨自一人時,我就情不自禁地要思考:難道我這一生就這樣下去,自己表演,也表演給人看,歡樂不是自己的,而自己的痛苦還要掩飾,帶著面具生活,永遠也不能面對真實的自己。瞭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幹什麼都比較專一,不喜歡敗在某個人的盛名之下,也不願意在藝術實踐上保持一個風格。包括為了生活的煩事而接觸宗教,我也是傾心盡意,一往有深情,我看《聖經》,看《古蘭經》,幾乎所有的宗教性書籍我都感興趣,但這也是在選擇,一直尋找能寄托我這顆心的歸宿。不瞞你說,在舞台上我雖然失去了自己,但在生活中我還沒有失去尋找自己的勇氣。
「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得道了,從『六字真經』中領悟了道。在對『唵嘛呢叭咪口牛』的永不停息的誦念之中,我忽然獲得一種被什麼提升起來的感覺:眼明,心亮,身體也處在一種異常興奮和快樂的動靜交融的感覺之中,我想:這是什麼地方?過去我怎麼不知道?我怎麼從來也沒有到過如此令人陶醉的地方,享受這種非物質的快樂?當這種感覺消失後,我必須又一次地從吟誦經文當中得到這種心靈的感受。於是,我從知道『大徹大悟』這個詞,到理解和感受到『大徹大悟』。後來,在學法的過程中,我知道這是『法喜』,所謂『法喜禪樂』就是指的這個。於是,我覺得我應該出家,我把塵世中的煩惱和過去名利場上的經歷、成績、榮譽、教訓全都拋諸腦後,我尋找原本蘊藏在我們每個人心靈之內的那麼一種清靜的覺醒,那麼一種安寧的本性的衝動,然後潛下心來,慢慢領會自然與人類生來即已具有的和諧與真諦。」
她說得真切,可我聽著有點玄,不是嗎?我等「檻內人」原無這般「出塵」之想。她顯然覺察到了我的疑惑,她讓我聽:「你聽,『唵嘛呢叭咪口牛……』你連起來一念,你能感到它是在迸發,是從無到有的迸發,像撞擊的聲音,也像誕生出精靈的轟響。」
聽她說到這兒,驀然,我的腦海裡現出前不久剛看過的一個科幻電影,講的是人類的起源,幾個探險者在火星上聽到一種不斷重複的聲音,由三個基本的音節組成,探險者突然領悟到這可能是人類遺傳基因DNA中的遺傳密碼,他們便嘗試著去符合這一聲音,於是奇跡出現了,一扇先人類的時空大門打開了,人類又重新回到了它的初創時期,而探險者也瞭解到了人類在星球上的起源的秘密。
李娜的說法和這個電影裡描述的聲音,何其相似!我不禁驚歎科幻和宗教的異曲同工。
我凝神望著李娜,一直在聽。
她生在我們的社會中,她長在我們的時代裡,進步的社會時代,尊重人的權利,尊重人的信仰自由,當她在頓悟之中尋找到一條精神解脫之路,不讓她在塵世的往事煩惱中徘徊,而在她認為快樂向上的溫馨環境中漫步,遨遊,這是一件她值得去做的事情,也是一件我們值得為她高興的事情。我們可否這樣認為:她真的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一條即使不是真實的至少也是通往真實的道路。在這條路上走的並非她一個人,然而這一點也不能掩蔽她的獨特性,恰恰相反,她的獨特性正是由此表現出來,她正是在這樣一條道路上找到了真實的自我……她沒有迷失本我,又找到了本我,這該是何等令人神往的境界。
我在聽,也一直在想。
想到小歌星謝津墜樓而去,想台灣歌手張雨生酒後飛車以至於「黃鶴一去不復返」———由衷地感歎道:人啊,要珍惜生命,珍惜自己,過去的一切不會形成開創新生活的障礙,低級的享受也並不妨礙高尚的追求!李娜推心置腹地對我說:「我是用整個的我來感覺到的,真的,我的心———回家了。」
她一點也不講她的歌,她一點也不講過去文藝圈兒內的恩怨,她也一點不問及同道同仁的緋聞軼事,她一直在講法,一直在講道。顯而易見:她在道中,法在她中,道與法在她這裡已經達到的結合幾乎是完美的。
李娜的媽媽坐在她的身邊,我和李娜聊著聊著,漸漸淡漠了她出家的僧侶印象,還是覺得她像個孩子。李娜告訴我,媽媽擔心她,到這裡住在一個朋友家裡,她經常看望媽媽,媽媽為她煮一些飯菜吃。我說:「李娜,你真不容易,人得需要多大的毅力才能捨棄塵世間的物質享受,而遁入空門去修身養性呀!」李娜說:「這應該全在你的頓悟之中,你一旦頓悟,會覺得擁有的遠多於你失去的。」我說:「半天了,你一點也不談你的歌,你真的全忘卻了?在你的生命中,應該有一大部分屬於音樂。知道你的人,源於音樂,佩服你的人源於音樂,想念你的人們還是源於音樂。你知道谷建芬老師說你什麼嗎?她說:李娜在《青藏高原》的演唱中,表現出某種高原性的東西,但這還不是她音樂才能的全部。我們許多的音樂人都是通過她的這首歌,重新又認識了李娜。我們很惋惜她出家。」說完這些我觀察李娜的反映。
李娜思忖了半晌,搖搖頭說:「不矛盾。在錄製《青藏高原》的時候,唱到最後我也是淚流滿面,不信你問張謙一,光為那歌詞和曲調我還不至於,我覺得自己終於體驗到了一種內涵,和我現在的追求非常吻合。」
看她要回憶起過去的事兒了,我趕忙遞去一些我從北京來的時候就為她準備的,她演出的一些劇照。她一張一張地拿出來看,並且告訴媽媽,這張是哪一次,那張是哪一回。看完以後,又還給我。
我是帶給她的:「怎麼?你不要?」
她笑了:「不要。這些東西我都扔了,北京家裡的東西也全不要了!」
我愕然許久,怔怔地望著她的媽媽,李娜的媽媽默默地挑了兩張照片,珍惜地收起來。
我很想知道她靠什麼生活,你生活中再有追求也得過日子呀!美國的寺廟裡給工資嗎?這兒的化齋怎麼化,是捧著缽盂站在路旁嗎?但是我不好意思直接去問,幾次話到嘴邊都嚥了回去,終於蹦出口的一句是:「你每天都幹些什麼?」
「唸經,作法事。」
唸經我知道,作法事又是什麼?
「就是幫人家集會唸經,打個鑼、察什麼的。」
我不禁想開個玩笑:好個李娜,放著獨唱不唱,卻跑到美國唱合唱……但是我馬上制止住自己。我提醒自己,信仰自由,宗教可以不信,但不該笑玩,更不能褻瀆。
其實,我挺佩服她的,比起無所事事,追名逐利的芸芸眾生,她原本擁有許多值得人們去神往的東西,但她不看重自己已經擁有的這一切。每天接受鮮花和讚揚,相對靈魂的寧靜又算得了什麼呢?她不願永遠沉浸在足踏紅地毯的喜悅之中,在她的精神追求中還有更大的喜悅———「法喜」,她為著自己的理想,斷絕了自己的過去,她的目光朝向未來,她所迷戀的境界,她所感受到的幸福,僅僅需要自己來建築———總之,她開闢了自己的道路……為我們的生活提供了另一種選擇,沒有什麼成就比這更是成就了!
儘管她很平和,對他人要求得已經很少,但我還是希望更多的人給我們曾經喜愛的李娜多一點祝福,當然我更希望她不迴避這一祝福!
這一天,我們聊了許久———我聆聽到了天外之音,至今這一聲音還在我耳邊迴盪……
附錄
《擁有「法喜」的李娜》一文在「昆朋網城」刊載以後,我接到很多電話,那些李娜的老朋友所表示出的激動與關懷確實令人感動,即使沒有見過李娜但聆聽過她的歌聲的人們也托我向她致意,這使我更加堅信:凡在大地上存在過的生命你就不可能把它連根拔掉。李娜的生命有一段時間曾在舞台上長成了樹,現在,她雖然淡出舞台,修身佛門,可還是未能被人遺忘,這意味著什麼呢?
但在這所有電話中最讓我感動的那一個卻是李娜本人的,她對此文內容表示認可,但對「大徹大悟」一詞卻做了新的闡釋,她說:「你在文章中說我已經『大徹大悟』,這是不太適宜的,至少對現在的我並不合適。也許在你們看來,我是『大徹大悟』了;因為我畢竟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成為佛教中人。但在我們佛門,我不過是剛剛開始在修行的階梯上攀登而已,離『大徹大悟』的境界還有著非常遙遠的距離。我這樣說並沒有謙虛的意思,確實,在佛門中比我感悟更多的人比比皆是。我需要學習的還很多,而有待研究的更多。我希望你在網上替我澄清這一點,我不願意在佛門同行中落下任何口實。」我聽後,忍不住想說:「李娜呀,你讓我怎麼辦才好呢?因為立足點與觀察角度不同,每個人對同一件事物會有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的見解;你覺得自己並未達到『大徹大悟』的境界,那是你以佛教崇高道義來要求自己呀!而我這樣還處在塵世中的人看來,現在的你不是『大徹大悟』又是什麼呢?不過,你這種求索不已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你不僅能贏得我等的尊敬,也會贏得同門的敬意。」